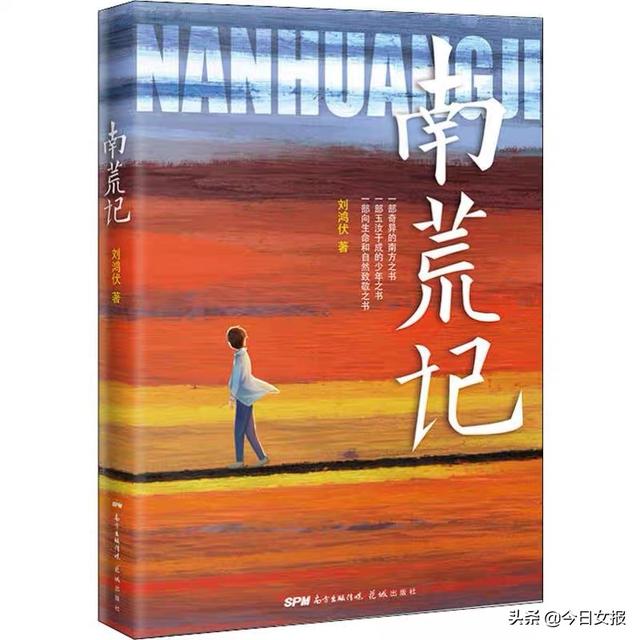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多年以后,当刘鸿伏回想起他考上大学的前几天,一切事物仿佛都充满了奇特的预兆。
“每个人落生到世上,都有一兜露水草养着,肉体凡胎一样能脱胎换骨,再乱的世道也可以卜见太平。”41年后,作家刘鸿伏终于在自己的著作《南荒记》中,借主人公刘务的口,说出他对那个年代的感悟与回味。
这个出生在湖南梅山大地的“南蛮少年”,终于用他最擅长的方式,用文字将这段贫困苦难而又奇妙无比的时光定格——通过少年刘务的视角,展现出1970~1979年间,中国南方山地的个体生命在成长中最真切也最奇异的原初影像。
南蛮之地的山村
刘鸿伏的家乡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这里自古便是似巫似道、尚武崇文的梅山文化区域中心。但在历史上,梅山区域的民族也一直是被封建统治者打压、丑化、歧视、侮辱的对象。
刘鸿伏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中国明代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就有“梅山七怪”。这“七怪”是由七种动物修炼成精的妖怪,各自身怀不同妖术,以最为厉害的白猿袁洪为首,帮助纣王攻击姜子牙所率领的周朝大军。最后女娲显圣,赐杨戬山河社稷图将袁洪收服。
这是一个具有民族志背景的隐喻。中国历代王朝一直视梅山为蛮荒之地,为了“山河社稷”的大一统,中央王朝对这片土地上所居住的“梅山蛮”,一直采取“以夷制夷”“怀柔羁縻”或是武力征讨的手段。
书名《南荒记》的“南荒”便是据此而来——南方的蛮荒之地。《南荒记》主人公少年刘务所在的小村,就是典型的梅山文化小山村。这个资水之畔的小村掩蔽在层层群山之中,有着清晰凸现的青山绿水,那里的方言至今保留着汉语的中古音,很多人认为万物有灵,巫风遍地。“我的家乡,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一条毛路进去。以前要出门,都是在资江边逆水而上,到县城就要一天,解放后有机帆船,如去县城,需逆水过几大险滩,行一天,六十里。”
在村民们上山伐木、田间耕作、放排渔猎的日常生活中,苦难、哀怨与忧愁淙淙流动。刘鸿伏书中的南蛮山地民族,有射雁鸣桑弓般的激越气质,坐看云起时的释然和不易察知的倔强生命力,叙事在宏大的漂泊感与隔世感中平缓推进,时间与地点渐渐游移并且模糊。一切如水,直至沁入心脾。
苦难魔幻的少年时光
贫穷、苦难、劳累、饥饿,这是刘鸿伏年少记忆中如影随形的关键词。书中的少年刘务,身上便有着不少刘鸿伏的影子。
“我从6岁开始就参加集体劳动,帮队里放牛砍柴挣工分。考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是个上好的劳动力,一年能挣5000多工分。我插秧是村里最快的,谁都比不上我。”刘鸿伏说,当年九口之家烧的柴,都是他一个人砍的。
跟书中的刘务一样,少年刘鸿伏也特别喜欢砍柴,因为砍柴是难得的欢乐时光,甚至可以自由飞翔——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上,这是苦中作乐的愉悦。
家里人多,虽然父母拼命劳作,但粮食远远不够。一年吃到头的红薯让刘鸿伏到现在闻到红薯的味道就反胃,“我弟弟三岁了还在‘打屌胯’,我穿的也是烂布缝补的‘百纳裤’,没办法,太穷了”。
在刘鸿伏的记忆中,儿时的生活还充满着奇幻和惊恐。南方的山地,环境险恶,物资匮乏。家里有个关也关不住的疯子叔叔,经常拿着刀要砍人,把几百斤的石头从山上推下来砸到房顶。母亲和祖母永远在吵架,待在村里晦暗处的寡妇、孤老、光棍和弃儿,“未卜先知”的少年刀生,充满着离奇古怪故事的老房子……这一切都被他写进《南荒记》里,变得更为离奇和诡异,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感。
书中村落里的意外也无处不在。砍柴人手中的斧头不慎甩了出来,正中刘务的额头,靠着邻居的一碗“强盗水”,刘务大难不死,但额头上留下了伤疤,变成了“三只眼”的形状。
没有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小山村,神灵和巫术是人们在苦难中唯一可以依托和祝告的对象。梅山地区普遍信奉梅山教,这是一种起源于古代湘中梅山地区、融合了道教法术和原始巫教特点的传统宗教,梅山的神灵也迥异于其他宗教,比如两腿朝天、双手撑地的猎神张五郎,手执斧头、面部黑黝的孟公菩萨……刘鸿伏甚至在书中写下了这些神灵们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这些来自于梅山先民狩猎生活的神灵们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充满烟火气息,和山民一样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小性格。
墓碑上的文学启蒙
《南荒记》的主线是刘务从6岁到16岁十年间的成长经历。事实上,这也是刘鸿伏自己的成长历程。对于历史来说,十年太短,稍纵即逝,但对于个体而言,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刘鸿伏说,当时的他非常渴望读书,也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少年强则国强,改变自己就改变了家庭、社会和国家,不然就会被埋没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虽然那是一个饥荒连着饥荒的年代,但刘鸿伏对书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渴求。
“那个时候实在找不到书来读,我们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就相约着放学之后去南山那片老坟地砍柴、读碑。”刘鸿伏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老坟山竖着几百块巨大的墓碑,从清代到民国的都有,“记叙逝者生平与美德的碑文大多文辞典丽、文采飞扬,碑刻以楷书和魏碑书体为多,真的是点如坠石、撇如长刀,美得让人目不暇接”。
读碑,让一群山里的穷孩子读出了先人的死生契阔、地老天荒。
在《南荒记》中,少年刘务踏雪借书,也是刘鸿伏的亲身经历。
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刘鸿伏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成为附近一镇四公社唯一一名大学生。录取通知书寄到队里时,大队书记却愤愤不平地问刘鸿伏的父亲:“你们家刘鸿伏考大学怎么不搞政审了?”
刘鸿伏告诉记者,他的母亲是“地主”成分,如果还像前几年一样,就算成绩再好,他也与大学无缘。在《南荒记》中,少年刘务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升初中的考试中,政治和作文被记零分。
“所以我很感激当年能恢复高考,它给了我们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机会,也给了这个国家向死而生的机会。”刘鸿伏说,1970年到1979年那十年,对于他个人和家族都是生死存亡,枯荣一瞬。
一部作品里的一代人
考上大学的刘鸿伏,一度曾被乡邻看作是“文曲星”。当时,他的一名同学得了精神疾病,但其父亲认为孩子是“中了邪”,跑来找刘鸿伏,要他写几幅对联带回去驱邪。刘鸿伏拗不过,拿红纸写了六幅对联,让对方拿回去贴在房门上,“说来奇怪,一个多月后,我那同学的病就好了,每年他都送酒肉来我家表示感谢”。
“我家门前的李子树,以前从来只开花不结果,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破天荒结了好多李子,黄灿灿好大一粒粒。我父亲说,这是帮我凑上大学的学费呢!”这个细节被刘鸿伏写进了《南荒记》的结尾。
“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写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烙印以及时代的巨变。”刘鸿伏说,1970~1979年,中国社会酝酿着巨大变化,“我的思想成长、生命成长在那十年里是最迅猛的。刘务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是生存在艰苦南方山区人们的群体成长。”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仿佛能听见时代的齿轮在咔咔作响。”刘鸿伏说。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并不挑读者,“十几岁的小女孩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都给我发来读后感,每个人都读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近期,刘鸿伏还将版税捐出,把书赠给怀化、益阳、永州、岳阳等地的部分中学,现在他打算再向长沙地区捐书。“我们绝大多人都是从贫困闭塞的乡村成长并走出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抱负理想和成长经历,但有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共同特点。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人生亦或人类最难以忘怀的阶段,少年强则人类强。我捐书的目的,就是想将百折不回、野蛮生长的精气神点燃新时代少年人的自强,也让他们了解长辈们走过什么样的路和人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察社会人情,乃至理解上代人的经历。”
《南荒记》俗世与神祗交融,人文与生态交融,叙事与写景写心交融,那么,如何理解书中众多魔幻、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的意象?就像书中留下的诸多疑问之一——刘务的堂伯娘,一位善良贞洁又受尽苦难的寡妇,为何会把生产队的牛推下悬崖?
“存在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就存在了。”在书中,刘鸿伏曾借刘务的口,在堂伯娘热闹到甚至有些荒诞的葬礼上说出这句话。
“这是理解整部书和那个时代的钥匙。”摸着额头上眼睛一样的疤痕,刘鸿伏笑着说。
刘鸿伏
当代作家、学者、收藏鉴赏家、书画家。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集和文物文化专著36部,其中散文集《父老乡亲哪里去了》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选入中国农家书屋目录;文物考古专著《遥远的绝响》入选“中华百年文博精华”;散文《父亲》与朱自清、梁衡等名家名作一并选入学教材三大版块之一的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文。还被选入高等职业教育语文课文和沪教版初三语文课文
另有《板桥上的乡愁》《寒鸟》《鹤》《梦里山河》《怀念一条狗》《一枕落花香》《读书的心情》等二十余篇作品被用作全国各省市高考模拟冲击题或选入人教版及多省初高中语文课外教材。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瑞典文出版发表。
《南荒记》是作家刘鸿伏积数十年人生历练和文字锤炼、厚积薄发的心血之作部梦幻般的长篇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个梦幻般的少年。
《南荒记》呈现出个体生命在成长中最真切也最奇异的原初影像:生长于南方荒蛮之中,那里的人至今用中古音讲话,认定万物有灵;亦生长于巫风遍地的人世角落,饥饿、天灾和人祸,包括诡异的死亡事件,如影随形。作品弥漫着苦难的诗意和无法言喻的意味。小说具有独特浓郁的南方农耕文化元素,有着个性鲜明的南方叙事特色,它既是一部生命成长史,也是一部社会时代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少年之书,一部南方之书,一部生命之书
《南荒记》在结构上,将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技法奇妙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方位、多视角的复式结构,故事人物首尾相连,浑然一体,又相对独立,你可能觉得在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能感觉在读《水浒传》你可以任性地充分享受阅读的快感,此书可谓开启了一种崭新的阅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