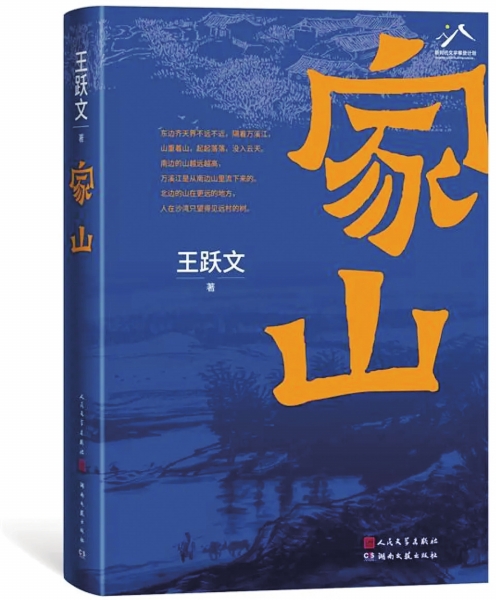
小说《家山》的故事发生在南方乡村“沙湾”,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劳作,老一辈中有年过七旬的乡贤佑德公,是村长也是道士的修根,年轻一辈里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齐美,留日归乡的扬卿,省城求学回来的齐峰等。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合作,抗战、解放战争……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在世俗又充满诗性的乡村图景中,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等冲突与争斗的命运变奏不时鸣响,一部波澜起伏的地方史诗徐徐展开……
“我以为文学的第一要义就在一个‘情’字。我爱我的家山厚土,我爱我的父老乡亲,我写作的时候可以说用心安放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因为语言在这里传达的是血肉和土地的关系。”作者王跃文说。王跃文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常常流泪,流泪是因为他对家山厚土爱得深沉。
撰文/潇湘晨报 记者 刘建勇 周华平
在沅水上游的山水田园画中再现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
“正月初六,天上好大的日头。桃香把糍粑皮、炒米放在几个大的簸箕里晒,人坐在地场坪晒着日头纳鞋底,手边放着响竹竿赶麻雀。西边屋角下,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登在柚子树上,隔会儿就会飞到簸箕边跳来跳去。桃香拿响竹竿敲几下,麻雀一哄而飞,又登上柚子树。”
《家山》的开篇,我们曾经熟悉,但又在嬗变中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乡村生活场景在这恬静、质朴的叙述中缓缓拉近。
因为作者是王跃文,熟悉的读者自然而然地把这明亮而温暖的画卷与雪峰山下叫溆浦的那块地域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是对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份》的承接和拓展。沈从文曾这样介绍溆浦——“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不靠洪江的商务,却靠一片田地,一片果园——蔗糖和橘子园的出产……”
王跃文在随笔集《喊山应》中认为沈从文对溆浦人旧时的营生说得颇有道理,并说溆浦农人自古相信一句话:人勤地不懒。溆浦人吃得苦,老天又赐下膏腴之地,这里的出产自然是格外丰富。这方土地一年四季从不空闲,凡南方应有之物皆能出产。
沈从文的蜻蜓点水,到《家山》这里就有了沉潜和激荡,那幅原先就有动又有静的画卷,有了引人入胜的生动的光影——“从柚子树下望过去,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田里长着麦子和油菜。山上很多野物,有狼、熊、豺狗、狐狸、野猪、野鸡、松鼠、野兔、黄鼠狼,凡叫得出名字的野物,山上都有。村里人到山里去,手上都会拿着家伙。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隔着万溪江,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南边的山越远越高,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
《家山》中的万溪江可以认作是溆水。《喊山应》中,王跃文曾说他和老辈人聊天告诉他们“溆水流入沅江,沅江入贯洞庭,洞庭汇入长江,长江奔向东海”,而老人们则告诉他说溆水西边有座鹿鸣山,山下有个蛤蟆潭,潭里有个无底洞,无底洞直通龙宫。《家山》中,万溪江的对岸也有个鹿鸣山,鹿鸣山下也有个传说中可通东海龙宫的蛤蟆洞。
《家山》中,主人公陈齐美是军人,常年征战在外,他妻子容秀则在老家沙湾。有一天容秀和小姑子贞一在家里的井边洗菜。贞一说嫂子映在井里的笑脸,哥哥在远方看得见,并解释:“我屋井里的水都会流到万溪江,万溪江的水都会流到东海。哥哥转战南北,他饮马处的水,说不定就有我屋井里的水。”
贞一颇有诗意的想象,就是王跃文的想象。齐天界下的沙湾村虽然深陷崇山峻岭,但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从沙湾村出去的人,为国家急难大事奔走、上下求索;国家层面上的任何一次波诡云谲,也都能在沙湾村的井水里照见动静。
从这个角度来讲,王跃文的《家山》,几乎聚全部笔墨于一村,实际上写的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的风起云涌。
以史笔为文,《家山》里的故事源自家谱记录的真实往事
“我只会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勾画乡村变迁和时世流转,完成乡村和乡村人物的命运表达。”四年前,王跃文在接受《芙蓉》杂志编辑杨晓澜的采访时曾如是说。彼时,《家山》正在创作中。
《家山》在出版前,一度被定名为“家谱”。事实上,王跃文动心写《家山》,最初就是因为他十多年前在老家翻看家谱,“特别是读到我的伯父辈、爷爷辈在1949年4月组织湘西纵队,跟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抗,迎接解放军进城。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这些革命青年在一个老地下党员的带领下一起成立(湘西纵队)这么一个武装,家家户户出钱出力,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读完家谱后,联想到自己小时候从奶奶、母亲和村里老一辈人那里听过的旧事,便产生了‘不能不写这部小说’的冲动”。
虽然是小说,但正如王跃文所说,他是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去勾画的,小说中,新中国成立前夕,沙湾村的人筹钱去辰溪买枪支持革命武装,这个出五十大洋,那个把自己的金耳环、金戒指和银钗子捐了出来,还有出谷子的、出土糖的,筹来的金额有多少、枪支武器买了多少,这些都是王跃文按照家谱记载的内容原原本本写下来的。“可以说我写《家山》就像写博士论文一样,以史笔为文。我写的是1927年到1949年期间的乡村生活,那个时候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乡邻之间的关系、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县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这些东西我都做过认真的研究,读过大量的史料,也读过大量研究专著。”王跃文说。
因为功课做足,随着情节的推进,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幕又一幕的乡村生活场景,在王跃文舒缓的叙述中得以还原和再现。就连书中主人公之间的信函往来及布告等官方文书,王跃文都是参照当时的真实信件和官方文书拟写的。加上小说中出现的《呼声报》也是在溆浦真实存在过,而马日事变、抗战、长沙大火等历史事件的无缝对接,让人以为真有那样的人与事件、信函与文书存在。
小说中福老太婆经常对女儿贞一说到的“我十五岁过到你陈家门上”,也是现实中真实细节的植入,现实中,王跃文的母亲常对他说“我十三岁到你王家门上”,而贞一的应对,也是照搬了王跃文自己对母亲的应对:“王家是您自己的,儿女都是您生养的!”王跃文的母亲是童养媳,到王家门上那天,那时王跃文的父亲才八岁,正打着陀螺,突然有人喊他爬到楼上,他爬上楼,跨开双腿站在屋门上方的楼梯口,王跃文的母亲低着头,从他的胯下进了王家门。这个场景,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家山》中,人物换成了十三岁的来芳和桃香九岁多的儿子齐明。
骨肉至亲的往事写入《家山》,让小说“家山”的意蕴更浓。正因为如此,王跃文创作这部作品时用情颇深,“我熟悉乡土,熟悉笔下的人物,我用心用情去写。当我写不同人物的时候,就会被人物附体,与书中的人物同悲欢、同哭歌”。
乡村伦理中真、善、美构成了《家山》的温暖底色
不懂乡村,无法读懂中国。不懂宗族,无法读懂乡村。
愚昧落后,一度是近数十年给宗族制或宗族观念贴上的一个标签,无论这个标签是否有失偏颇,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很可能我们大多数时候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总有某个时刻,你会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家山》中,因为王跃文的细致,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个机器在沙湾的运转。
故事开篇,山水田园画般的美好祥和气氛中,舒家坪的外甥舒德志来给舅舅四跛子和舅妈桃香拜年。饭吃到一半,酒才喝干三碗,村里有人敲锣,说舒家刀刀枪枪杀过来了。原本一起吃饭喝酒的舅甥散了,各自奔赴自己的阵营——“依沙湾老规款,碰着外村打上门来,哪家壮丁不上阵,打完架回来就烧哪家的屋”,沙湾的老规款如此,舒家坪的老规款也差不多。打斗中,外甥喊出了“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蠢话,舅舅让了他多次后,骂了一句朝天娘,取下马刀剁了外甥。
打斗死了人,官府的枪兵来抓人,德高望重的佑德公立字据做保山,说先打官司再讲捉不捉人,如果官司输了,保证把人送到。后来,擅长四六八句的桃香代表沙湾村去县里打官司,县知事判舒家坪寻衅滋事,沙湾人陈修权(四跛子)无罪。作为族中的灵魂人物,佑德公此后还在征赋纳税、救“红属”、抽壮丁、大洪水、乐输抗捐、办教育等村事上多有担当。
《家山》中,宗族力量在外部势力入侵或压迫时,它的保护和缓冲机制发挥作用。但,显然王跃文写《家山》不是给宗族制唱颂歌。
小说中,宗族家法之所以起到了一些互助互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佑德公、逸公等德高望重的乡贤。如果自私、贪便宜、霸租着不用交业(赋税)的祠堂田的扬高掌控着陈氏家族,沙湾会是怎样的沙湾?
《家山》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数十年的事情,彼时,宗族制已经不如以往强势,农会及各种新的思想已经在冲击和重新建构着宗族势力。20多岁的陈扬高因为是农会执行委员,在听说舒家坪的人打上门来时,可以腔口很高地要求乡亭叔侄拳头朝外打,“不管他,先打了再讲”。
祠堂是宗族议事、祭祖的重要场所。在20世纪以前,基本上是不允许女性进入的。但,在《家山》中,桃香进了祠堂议事。后来祠堂里办了新式小学,女老师史瑞萍和沙湾的女学生也可以进入祠堂了。
祠堂如此,宗族制、宗族势力受到的影响也可见一斑。这些变化,有来自国家层面上法治的推进,有来自文化新风的影响,还有来自宗族内部的新鲜血液、年轻力量的改良与革新。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鸿篇巨制的重大阐述里,总会反复出现这句非常熟悉的话。这大变局其实也发生在处庙堂之远的乡村以及乡村里大大小小的宗族中,以宗族制为基础的乡村伦理也随着这些变化重新建构。
成书早于《家山》之前的《喊山应》中,王跃文曾说他关于乡村的心境非常矛盾和复杂:“一方面,我对它有天然的感情,爱着那里的山水和人民;一方面我知道它的颓败和危机,内心忧虑。”王跃文曾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要有慈悲,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对乡村的热爱和忧虑,加上一贯的文学坚持,王跃文在《家山》中展示的便是乡村伦理中真、善、美的温暖底色,这是一种怀念,也是他希望能够看到的传承。
对话
“文学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有能力把每一代人活过的样子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

王跃文。
潇湘晨报:2022年7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支持项目名单公布时,我看到您的作品是《家谱》。
王跃文:这本书的名字当时我还没确定,《家谱》只是暂定名。我写这部小说最早的动因是我看我们村的家谱,《三槐堂王氏五修族谱》。族谱中有历代以来的显祖传记,上次修谱到新修谱这段时间族里重要人物也会单独作传。这是1998年修的。当时,我还年轻,看的时候不太在意。大概10来年前,我再看,看到我爷爷辈和叔伯辈的事迹,对我触动非常大。
我们村里有个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先辈,他是书中齐峰的原型,按辈分,他是我的伯父。长沙“马日事变”以后,他冒着血雨腥风回到县里,重新建立了地下党组织。齐峰的原型地下工作经验十分丰富,每次都逃过了抓捕,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直到1949年三四月份出来拉起一支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后来成为湘西纵队中的一支。其实,齐峰的原型,在外的革命工作经历更丰富、更复杂,但因为不符合我这部小说的叙事逻辑——这部小说是以沙湾村为中心去写的。
中国人自古都很重视家风建设。每一次修订家谱的过程,就是对整个家族历史进行总结的过程,家族的精神在家谱中得以传承。书名最后改成《家山》,比当初暂定名《家谱》气象更阔大些。我写的是我的家山,我也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家山,我写的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山。
潇湘晨报:书中其他人物,如陈齐美、陈贞一等人在外面的事情也只是通过家书或者战报简单提及。这些人物精彩故事的舍弃,有没有觉得心疼或遗憾?
王跃文:那倒也没有,这要服从小说的结构,太散了也没必要。再一个,小说要有疏有密。《家山》写的只是沙湾村,范围最多辐射到了竹园村和县城,尽管是这样,我觉得这部小说的内容还是扎实、丰富、辽阔,时代感、历史感很强。
潇湘晨报:确实,我在阅读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写的只是一个偏僻的村落,但国家的大事、重要事件都在村里看得到折射。
王跃文:对。按照我个人的主观意识考虑写作——我曾经说过两句话,写小说一是凌空观照,一是贴地写作。凌空观照就是对写作对象有高远宏阔的把握和思考。贴地写作就要落实到人物、落实到细节、落实到故事。大量大量鲜活的细节构成情节,情节推进故事,然后完成小说。我是这么思考的。
再一个说,我们过去对社会的认识太局限于某一种史观,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我是刻意跳出这种史观对过去、对生活的概念化的先验定义,用我自己对生活特性的认知,再去通过文学去艺术地呈现。所以,硬是要说的话,这部小说一方面是部社会生活史,也是一部乡村民俗史、乡村繁衍史,当然,也是时代变迁史。
历史有更宏阔的东西,天地之间万物生灵一切过往、一切喜怒哀乐,都是历史。过去百年,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历史的推进是一个混响的过程,而不只是政权的更替。
潇湘晨报:以前我们提到乡村,有些人可能首先会联想到愚昧、落后,但其实就像您在《家山》中写到的那样,乡村也是产生和输出先进人物、优秀人物的地方,即使在乡村里头,也有佑德公这样很开明的乡贤。
王跃文:我读我们溆浦的党史,发现早期参加革命、参加地下工作的,大多是乡里的富家子弟,他们出去读书了,有见识了。
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亲情纽带连接起来的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从古至今有一些好的价值观念流传下来,约束所有的人,所以一般人不会在自己村里太为非作歹。所以,过去有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一种很切实的生活哲学;另外,一个人哪怕他在外面混得人五人六、趾高气扬,一旦回到老家,都会夹起尾巴做人。这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好的风化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潇湘晨报:您前年出版的《喊山应》,现在看来,有点像是《家山》的创作谈了。《家山》和《喊山应》的创作,有没有存在一些呼应或者说相互成就?
王跃文:《喊山应》是我回望故土、梳理创作心得的一本书,其情感脉络和文学理念自然会在《家山》里有所体现,这两本书的精神气息相通。
潇湘晨报:读完《家山》,回过头再看您在《喊山应》中写到的“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就特别有认同感。这应该就是文学的力量。据您的观察,重新建构后的乡村伦理今天是否还是我们乡村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乡村伦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来自哪里?
王跃文:我们对今天的乡村文明有新的定义,其时代性和先进性得以凸现,但传统文化根脉永远是乡村文明坚固的基石。我说过,乡村中国是最大的中国,这是由乡村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深厚的文化根脉所决定的。文化是延续的,它会不断发展,但根基不会动摇。乡村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定性。
潇湘晨报:《家山》中有大量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这是否是在向您接触到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致敬?作为您的枕边书,《红楼梦》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王跃文:作家会受到很多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我的确非常热爱《红楼梦》,但我想说的是自己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较大,包括语言方式、审美趣味、气韵、气象等等。我喜欢写日常生活场景,写烟火人生,写细腻微妙的情感,写平凡日子里令人动容琐碎,这些都是元气丰沛、真气淋漓的人间景象。文学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有能力把每一代人活过的样子有声有色地呈现出来,把每一代人的精气神传扬下去。《家山》该铺陈处不厌其烦,该简约处惜墨如金。
潇湘晨报:您曾说过,熟稔的乡村,也许正在教您重新认识生活,《家山》是否是您重新认识生活的一个结果?除了《家山》外,还有没有别的来自重新认识生活带来的收获?
王跃文:《家山》是故乡给我最大的馈赠,我感恩我的故乡。我随着年岁增长,对故乡的认识越来越深,对那片土地上的人越来越怀有深切的情感,对父老乡亲身上的文化印迹越来越有新的体认。我写作《家山》的过程,就是回望故乡的过程,也是再次认识和发现故乡的过程。我笔下的人物,勤劳、智慧、勇敢、友善、仁义,这些品格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样子。
潇湘晨报:《家山》中,无论是您代书中主人公拟写的对联、引用的《诗经》的句子,还是大量方言词汇的运用,以及乡村景色的描绘,让我感受到了来自时间深处的汉语之美,联想到在您的一些讲座中听到的您对古诗词、对鲁迅作品经典片段等脱口而出的背诵,深感《家山》也是您对汉语、对我们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回馈。
王跃文:汉语是人间最美的语言。王国维说,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这种汉语韵味和魅力,只有中国人能懂。我沉醉于汉语之美,写作《家山》的过程中,不放过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很多方言土语其实是古语,高古雅致。文学作品中将方言土语准确的汉语符号找出来,便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比如,湖南很多地方把“烤火”说成“揸火”,我认为“揸火”比“烤火”更准确。揸,指的五指张开。“揸火”是对人们围火取暖状态的形象描述,非常有场景感,这就是简约的文学表达。汉语中有许多存在语法和逻辑错误的表述,人们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承认其合法性,比如,“晒太阳”其实是“太阳晒”,“吹风”其实是“风吹”,“烤火”其实是“火烤”。“揸火”就真是“揸火”。
来源:潇湘晨报
编辑:宋芳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