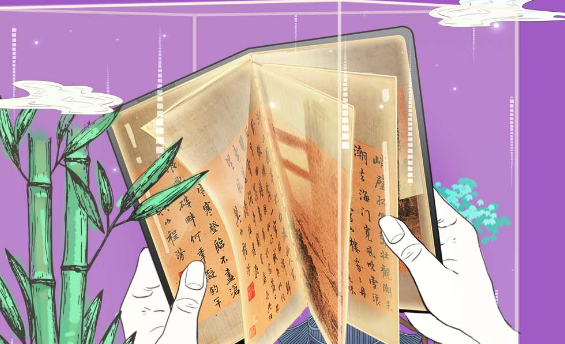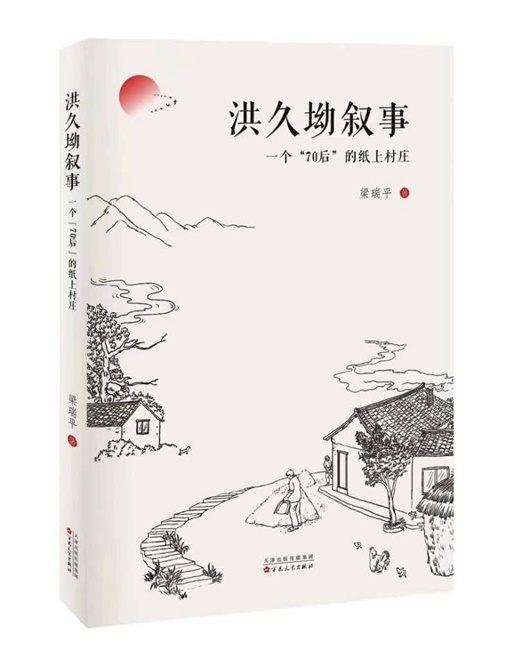
在中外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乡愁(乡情)都是永恒的书写主题。写作者既有舞文弄墨的专业人士,也有数不胜数的平民百姓。体裁也是丰富多样,有散文、随笔,也有诗歌、小说等。他们的诉求,既是抒发自我,也是记录时代;既是留存记忆,也是寄托情怀。
也许因为研习的是历史,从事的是新闻,所以这种经历使瑞平兄有着记录的自觉。细读《洪久坳叙事:一个“70”后的纸上村庄》书稿,我不得不为他的努力与坚持点赞。毕竟,对于求学、对于进城;对于童年,对于中年;对于时代,对于世相……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如果每个人都拿起笔,写下自己独到的观察与领悟的话,那就是往历史的硬盘里增添了一份素材,使得历史更加丰富多彩、多元充盈。
有人认为,书写乡土,追根究底是在书写一种生活,书写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个著名的观点,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瑞平先生的乡土书写,应该是在试图解决第三种关系。我们可以感觉到,出身乡村的一些人在进城过程中难免有不适,甚至是困窘。虽然忙忙碌碌,有成功亦有失败,最难受的或许是灵魂,总觉得身心无处安放,难以妥帖。而通过书写过程本身,紧张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纾解或释放。
在本书中,作者用文字回答了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回答了生活本身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他通过记录让我们知道,生存在江南湾村洪久坳的普通乡民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生活的,这也间接折射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两三代人所生活着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面貌。
尤其是,作者的写作跳出了小我的情感抒发,以超拔的眼光关注乡村里曾经有过的手艺人木匠、篾匠、铁匠、砌匠等,那些故乡生民离不开的器物如镰刀、扁担、风车、算盘……还有双抢、过年、赶墟等日常生活。
我最为欣赏的是关于乡村手艺人的“一人一世界”部分。随着时代的演进,有些手艺被淘汰,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但毕竟是一门门活泼泼的技艺、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这些手艺人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关联着大民生,他们的存在曾经不可或缺,他们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
独具匠心的还有以器物为切口,回顾过往的乡村时光。如果器物能够开口说话,那么,它们无疑是来自生活现场、历史场景最有发言权的证人,见证过悲喜、进退,凡人的打拼以及始终不曾泯灭的人性,传承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
当下乡村的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赋予了乡土书写许多新的课题。评论家汪政曾经把乡村写作分为“在乡式写作”“离乡式写作”及“返乡式写作”。那么,明显处于“离乡式写作”境地的本书作者,该如何选择叙述的立场?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笔下既有挽歌式的,也有反思性的;有一些抱憾,也有不少无奈……但在我看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价值观的选择。
有人认为,当下的乡土写作面临着几种困境。譬如经验表达的趋同化,以及乡土书写价值的同质性。至于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只是需要更多人的探求与尝试,不断丰富写作的主题与样态,并以鲜明的个人特色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注脚”,是一个人对乡土社会及社会变迁的“管中窥豹”。
我来了,我看见,我书写。若真能如此,那么,一个人的日子应是充实而无憾的。
(本文系《洪久坳叙事》序言,有删减,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