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了十多年的童书,在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童话大王郑渊洁直指“童书作家违法进校园售书”问题,炮火“蔓延”至当红作家“曹文轩”“杨红樱”。
当中国90%的出版社都在做童书,当研究者以“儿童文学图书重复出版现象”为研究对象时,几乎可以看见“逐利”和“着急”情绪在童书出版市场上的蔓延,而郑渊洁所爆料的“问题”或许不过是童书“火爆”背后的冰山一角。可是,热点终有一天会被新的热点所覆盖,而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却扎扎实实地面对着如何“阅读”的问题。在童书空前繁荣的时代,如何从鱼目混珠的书海中,找到好书?如何阅读历史中的“经典”?
今天,我们将展开一场开放式讨论,这场讨论不会提供“标准答案”,但会帮助提供一种理解“童话”,选择“童书”的思考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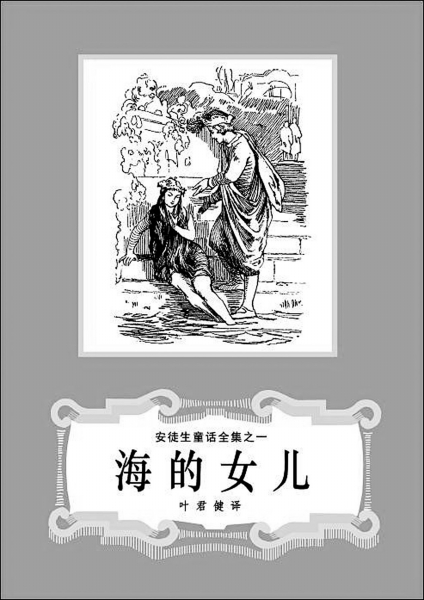
“不是因为一个故事够经典,所以大家都应该去喜欢”
先从“过去”说起,当“经典”被“重新阅读”,“意见”开始发生分歧。
最近一位网名叫“轻成一只飞燕”的妈妈在微博上说:“我从来没有给我女儿讲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当女儿在故事机里听到“小美人鱼化成泡沫”时,她赶紧把开关按了,并对女儿说:“别学小美人鱼,鱼类智力不高,你是人类女孩,你有脑子,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
她反对《海的女儿》的原因有三:第一,生命观错位,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第二,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用美丽的长发、无法说话、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爱情”?第三,所有王子公主式的童话不适合讲给女孩子听,因为生命不只有嫁给王子这一种结局。
“轻成一只飞燕”的较真,引来无数网友留言,支持反对皆有。陈丹在《<海的女儿>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引出《海的女儿》中的一段话:“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
陈丹写道:“这段话和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段话何其相似:‘对于女子而言,婚姻是唯一和社区融合的途径,如果没人娶她,从社会的立场看,她是被浪费了。’女性只有通过婚姻才能结合于社会,而人鱼只有通过和人类的婚姻才能得到不灭的灵魂。”
而反对者认为,“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只会觉得海的女儿很可怜很善良”。同时,“不应该剥夺儿童对爱与幻想的权利,不要用成年人世故又圆滑的思想去代入孩子的想法”。
当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儿文学图书事业部副主任、副编审周亚丽对7岁的儿子龙龙讲述这个故事时,龙龙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这个故事”,还说:“小美人鱼应该先跟家人说再去海面上找王子,放弃生命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她还有爱她的家人。”
“我觉得这是今天的孩子对生命观的一种初始解读。”周亚丽说,“《海的女儿》这个故事是安徒生由一部小说触发的灵感,结合自己一次失败的爱情经历所写的童话。他首次出版已经距今180多年了,21世纪的人对19世纪的童话来进行解读,不可避免会带入今天的价值观。去做阅读引导还是多让孩子说话,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用一个成人化的视角来规约。跟我儿子聊了之后,我才知道他并不喜欢这部童话,所以不是因为一个故事够经典,所以大家都应该去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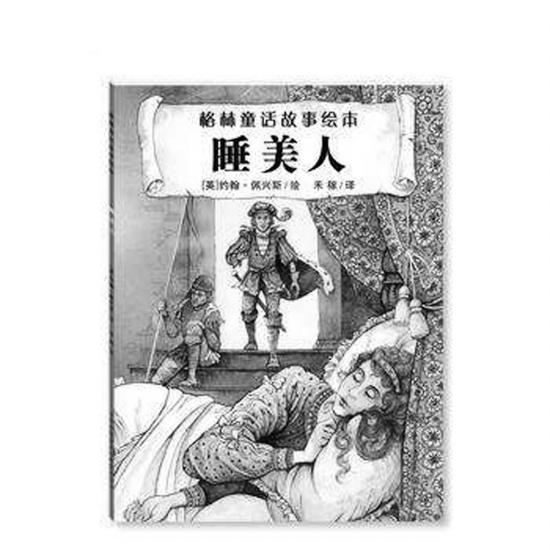
《皇帝的新装》和《睡美人》,一开始不是写给儿童的
如果简单用“好”与“不好”来判断《海的女儿》,似乎略显武断。
当周亚丽跟儿子龙龙讲《海的女儿》时,他的反应是:“我看过的《海的女儿》有两个结尾,一个结尾是小美人鱼跟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个结尾是小美人鱼回到大海里跟姐姐们在一起。”周亚丽意识到:“我们今天对经典童话故事真的做了很多版本的改写。”
这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思考路径,那就是历史的维度。常常用“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童话,一直是今天的模样么?第一个“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意义和初衷究竟是什么?
“王子走近沉睡的公主。她躺卧在织锦高台天鹅绒的王座上。他叫唤她,但她似乎并无知觉,好像陷入昏迷。他端详着她迷人的美貌,忽然感到热血沸腾,血脉贲张。王子于是将她抱起,带她来到床边,趁她沉睡时,他在床上首次尝到爱情甜美的果实。他完事后便离开了公主,回到自己的王国,在繁重国事中不再想起这段插曲。”
这样的桥段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睡美人》?这是雪登·凯许登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中的一段文字,它出现在1634年意大利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著名的《五日谈》里。
“一天,三个骗子走到国王跟前,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织造呢绒的能工巧匠,其中一个更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是婚生子女,都能看见他们织的呢绒,但若是非婚生子女,那就永远也看不见他们手艺的结晶。国王一听,不禁大喜……他下令把三位工匠安置在一座宫殿里,并在那里织造呢绒……国王先后派遣了他的多名贴身侍从、近臣去观看织造的进展情况,每一位回来以后,都对国王狠狠地夸奖了一番呢绒如何精美,如何漂亮……于是,国王自己亲自去观看这了不起的织物,可是不幸的国王什么也看不见,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唯恐被人发现这个事实,从而失去自己拥有的王位。国王便更加卖力地夸赞起来。于是,这三个骗子用那种所谓的神奇布料为国王做了一身‘新装’,当然,这美丽的‘新衣’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到,包括国王自己在内。可是人人都不愿承认自己看不到的事实……”
这个故事是不是同样很熟悉?这个故事还不叫作《皇帝的新装》,这是14世纪西班牙散文家堂胡安·曼努埃尔的代表作《卢卡诺伯爵》中的一个故事。
“在原初面貌里,童话一开始并不是为专门为儿童所讲述、所创作的故事。”李慧在博士论文《童话论》中写道:“民俗学家已经通过严密的研究发现,民间童话/民间故事(folklore)诞生之初,其目的并非为了儿童的娱乐,更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口头民间故事最早出现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成人间讲述,而当口传文学被记录下来,开始成为书面的民间童话之时,这些童话故事也依旧不是写给儿童的。”
实际上,“早在格林兄弟的时代之前,儿童文学几乎不存在,也没有所谓的儿童,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历史学者亚力士(PhilippeAries)指出,所谓儿童期和青春期是人类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几世纪以前儿童往往夭折,因此除非他们证明自己有生存的能力,否则鲜少有人会关注他们。一旦有生存能力,他们便立即被视为成人。贵族的‘儿童’穿着像个小大人,燕尾服、撒香粉的假发、调整身材的紧身束腹……”美国作家凯瑟琳·奥兰丝汀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一书中写道。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说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像儿童文学这样的东西当时并不存在。其实,在文学作品里‘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通常是淹死、窒息而死或遭遗弃……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为什么中国童话常被认为“爱说教”?
直到格林兄弟的出现,民间故事被剔除了“性”“粗俗”“暴力”等“少儿不宜”的内容,真正面向儿童。
而他们改编的一大动力是“赚钱”,原本他们搜集民间故事和传说是用于学术研究,但因财力不足屡遭磨难,于是转而改编童话解决经济问题,影响至今的《格林童话》诞生了。
“于是,一条清楚的发展脉络就呈现出来。民间童话从民间故事的雏形中逐渐脱离出来,越来越靠近儿童文学,最终成为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一种文学种类。格林童话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正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继承着民间童话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而来的渊源,成为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民间口述文化进行搜集、整理的自觉……另一方面,它成为把童话转化为儿童所专有,成为有目的地以这种样式去‘教育’儿童的第一次开拓性的尝试。正是因为这样,格林童话一度几乎成为了‘童话’的代名词,也开启了被后世称作‘教育童话’的新篇章。”李慧在《童话论》中写道。
无论是童话还是“童话”二字,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直到今天,西方外版童书也更被家长所青睐,也成为出版社争夺的焦点,家长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国内的许多童书说教意味太浓了”。
多年耕耘童书领域的周亚丽说:“我个人觉得优秀的外版童书对人的存在、情感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是观察和审视得比较细致的,显得更加真实能触发共鸣;为什么老觉得国内童书过于说教?我觉得更多来自于话语方式总是自上而下的,有一种主体意识的错位。”
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李慧认为与它在中国的传入和诞生息息相关。“童话”这个词语第一次真正进入中国的视野,始自商务印书馆1908年11月开始发行的一套《童话》丛书,这套丛书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的相关民间童话样式的小说、故事加以改编重写,这引发极大的关注和讨论。
“童话为当时五四作家所青睐,绝大部分原因亦在于他们所观察到的童话对于儿童莫大的吸引力和教育性。于是,中国创作童话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生’的无限贴近于现实的发展之路。”李慧说,“《稻草人》是如此,《长生塔》是如此,甚至张天翼用那样幽默、滑稽、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述的《大林和小林》、《金鸭帝国》等也是如此。这条路就这样延续了下去,一直是中国童话的主流。所以,中国的创作童话,离现实更近,离幻想较远;离教育更近,离娱乐和游戏则较远。这一面貌甚至影响到民间童话的创作那边去,葛翠琳做《野葡萄》、洪汛涛做《神笔马良》,等等,其中还都是反映着普通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与斗争。”

童话的意义?“让他们愉快”便是最大的实益
今天,在人们心中,童话与教育似乎依然有着“天生”的关联。
“读这个故事孩子可以学到什么?有什么意义?”或许依然是大家选择童书思考的问题之一。
而百年前,周作人就说:“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我说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它的作用,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至于其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
但当时的许多童话让周作人很不满,他说:“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
如果再回过头去看看“童话”的诞生:“当童话还处于人类的童年期,和神话、传说等共同位列于民间口传故事之中时,它就是以丰富的娱乐性和游戏性与神话、传说的严肃性相区别的……童话的‘快活’,就是游戏精神和娱乐性的充分体现,成为它与别种文艺绝对不同的质素之一。”李慧说:“可以想象,在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讲述民间童话都是在纺织工坊、田间地头、铁匠铺子,以及小酒馆等民众群体集中的地方倍受欢迎的一种自然而且便宜的娱乐方式。在流传之间,同样一个故事,不仅传播广远,更是因为经过了不同的讲故事人的嘴巴,经过了这张嘴巴的加工、修饰、改变,渐渐有了复杂多样的面貌。”
今天,童话常被人取笑为“幼稚”的读物文本。实际上,不是有了“会说话的动物”就是童话,创作了《霍比特人》《魔戒三部曲》的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曾在《论童话》中提出童话的真正质素:“仙境的魔力不是体现在仙境自己身上的,它的美德体现在一些操作层面之上,其中就包括着对于人类本初愿望的满足。这些愿望之中,其一是去探索时间和空间的深度;其二是与别种生命体存在的沟通交流。一个故事只有是在完成着对这些愿望的满足——不管它有没有使用魔法或者类似手段——相应地它也就越能靠近童话的真正味道,具备童话的真正质素。”
李慧认为,托尔金的这段话点出了童话最重要的三大质素之一,那就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深度探索、对时空深度的追索以及对异类生命的发现和沟通。“这难道不正是人类永恒的认知和追求吗?不仅仅童话如此,其他文学样式之中,甚至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的求知,不都在做着同样的事么?也正是因为人们所持有的这一美好愿望,所以童话的另外两大重要质素——想象力的无穷张扬和游戏精神赋予的乐观向上,也就显得格外出色。而对童话飞扬的想象力以及快乐的游戏精神,也只能放在这一语境中去考察才能显示出它的非凡。”
对话
周亚丽:童话当然不是只能包含真善美
潇湘晨报:近几年,少儿图书市场火爆。但据报道和统计,目前大部分家长更倾向于购买国外的绘本和童书,真实情况如何?
周亚丽:少儿图书市场的确是经历了黄金十年,然后又遇上了二孩红利,所以造就了一个很火爆的景象。其实早在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国内的图书市场上就已经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外版童书,如今千万级的畅销书《窗边的小豆豆》,1983年就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在童书的内容制作和出版理念上,国外确实领先了我们很多年,专业化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其实这是儿童心理和教育理念的一种折射。所以在高知父母人群中,外国引进童书甚至是国外原版童书相当受欢迎。引进版的童书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非常优秀的,但也有跟风之作,一流的外版童书也被引进得差不多了,新产出的作品又需要一些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然而这个市场需求又在井喷。所以我们近年就可以看到很多二流三流的外版童书也被引进到国内,就是商业逐利的本性所驱动的,现在我们在大力推动原创,我相信本土作品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崭露头角。
潇湘晨报:童话只能包含“真、善、美”么?什么时候可以同孩子讲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什么时候可以和孩子谈“性”“背叛”“欺骗”?
周亚丽:童话当然不是只能包含真善美。其实《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有不少暗黑的成分,德国的童话里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残酷的内容,甚至是血淋淋的,但是这些不太被避讳。我曾经给我儿子讲过一个德国的儿童故事——因为孩子喜欢吸吮大拇指不听劝告被剪掉大拇指。他听完哈哈大笑,他不认为这种惩罚是有效的。他说,“他还有另外四根手指可以吸呀。”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足以支撑起残酷、疼痛这类概念。所以,我们其实是依据我们多年的个体经验来替他们做了判断,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复杂化了。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话题都可以逐渐地去说给孩子听,一些人格塑造、性格培养的绘本里就有涉及到这些,它们用故事性强的,比较隐晦、处理得比较美好的方式,在不增加心理不适感的方式下去说的。你首先得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灾难,有伤害,有死亡等,事情也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但是可以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许孩子一个期待,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撰文/潇湘晨报 记者 赵颖慧)
来源:红网
作者:赵颖慧
编辑:宋芳
本文为湖南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