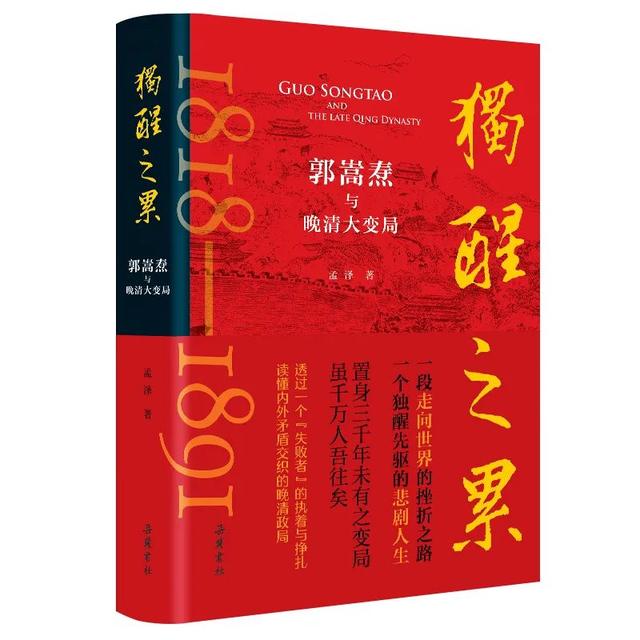
文/余孟孟
谈及中国近代史上改革者们的个人遭遇,史学名家陈旭麓先生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说:“尤为凄惨的是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西方)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骂中步出国门的。作为洋务同辈里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庚子事变正盛之际),有人还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这般遭遇,的确让人唏嘘感慨。可是,郭嵩焘何许人也?他的生平、事迹、才智、命运,究竟如何?大多数人对个中详情恐怕都不甚了解。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改革者相比,不管是被梁启超称作“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李鸿章,还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郭嵩焘的知名度和重要性都要逊色很多。然而,倘若拉长历史的视线,站在今天“后见之明”的立场来看,就可以透过郭嵩焘身上披挂的诸多误解,而看到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物。又倘若挖掘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思想变动层面探求近代中国的变革历程,就可以发现,郭嵩焘虽改变历史似少,但提醒后人实多。可以说,从19世纪后五十年的“短历史”来看,郭嵩焘的实际影响力有限;但是,从近来以来至今的二三百年的“长历史”来看,郭嵩焘的启发意义巨大。尤其是在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局势当中,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郭嵩焘可能是一把非常合适的思想钥匙。
1.独醒之累
当代知名学者、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先生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最近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源于十多年前孟泽先生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所作关于郭嵩焘讲座的文字实录。十多年来,通过讲、读、写,删、改、增,今天呈现在大众面前的这部以“独醒之累”为主标题的郭嵩焘大传,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孟泽先生以情理兼备、文质相融的笔法,用40余万字的篇幅,深描出了一位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之中,求学、做官、隐居、出洋,用自己赤子般的直率与纯真面对家国大事,将自己的生命积极融入时代大势之中,却屡屡遭受挫折,不断面对误解,只能背负“独醒之累”的时代先知的悲剧人生。
郭嵩焘是一位饱受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他在生前就已背负骂名,身上被泼满了“脏水”。这样的人,自然也很难得到家乡父老的尊崇。孟泽先生就说,他曾去郭嵩焘的老家湘阴、汨罗一带,却几乎找不到郭嵩焘的“遗迹”。而同样作为湘阴人,又与郭嵩焘同时代且一生相交甚密的左宗棠,却得到乡人格外的重视。左宗棠的能耐、才识和功业当然是百年难遇的,但是孟泽先生却自信地预测:“五十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这当然不是一种武断的轻言,而是孟泽先生对郭嵩焘本人及其所处时代大变局,作全面的考查、同情的了解、严谨的研究之后,得出的清醒判断。

2.三重“返回”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一书,绝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并非单单是为某位历史人物正名或“平反”,而是反思历史之作,感怀时事之作,探寻幽微人性之作。
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三重意义上的“返回”。
其一,是返回历史现场。“光绪十五年(1889年),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开始撰写回忆录性质的《玉池老人自叙》。写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他行将去世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二十日,才于病中收笔。……”孟泽先生用简洁细腻的文笔重构出郭嵩焘所处的历史时空,让读者可以通过文字和脑部画面的形式返回那个大变动、大震荡的历史现场,去和当时的国人一起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传统中国的出路等问题。
其二,是返回中国传统社会。从家族家风到科举制度,从官场规则到人际交往,从民俗民风到社会心态,孟泽先生通过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精神风貌,如卷轴画一般在读者面前缓缓打开,让今天的人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先人曾经面对和生活过的社会。
其三,是返回有血有肉的真实人性。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是被后人“书写”和“重构”出来的,若有不慎很容易会给人一种抽象或失真的感觉。曾经一度,我们读到的历史人物,是脸谱化的,是非此即彼的,特别是在历史大变动之际,爱国者与卖国者,忠臣与奸臣,好人与坏人,英雄与罪人,被我们划分的泾渭分明。而事实上,历史人物也是人,也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是非对错。在这部书中,孟泽先生笔下的“男一号”郭嵩焘以及郭的“重要他人”,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曾国荃、严复等人,他们个人的优长与局限、性情与心机、勇气与退缩,重情与寡义、良善与残酷等,都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真实人性的不同侧面。以此为镜,我们也可以映照自己的人性。
3.卖国还是爱国?
作为大变局时代的历史人物,郭嵩焘身上最大的污点,恐怕就是被时人和后人指摘的卖国行径和崇洋媚外心理。可是,判定他这项“罪名”的证据却并不见得能站得住脚。
比如,作为郭嵩焘出洋副使的刘锡鸿,就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列举了郭嵩焘卖国的“三大罪”:其一,郭嵩焘在参观英国某炮台时,寒风凛冽,英军提督见郭嵩焘打寒噤,就拿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的身上。而刘锡鸿认为,即使冻死,也不能披洋人的衣服。其二,某次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屡取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其实看不懂。其三,在某场合,见到巴西国王,郭嵩焘擅自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效果君主致敬?
今天看来,这些代表文明的礼节性行为被看作卖国行径,实在可笑至极。可是,返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和刘锡鸿认识相近的大有人在,因为要知道,我们今天国人所达到的某些普遍见识,是近代以来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所取得的。郭嵩焘的挫折是那个时代的挫折,郭嵩焘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王元化先生就在《郭嵩焘与湖南新政》一文中说过:“郭嵩焘是早期变法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不仅远远超迈倡导洋务运动的前辈,就是同时期的维新人物也难以和他比量。”当代著名编辑家钟叔河先生在《论郭嵩焘》一文中也说:“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
和王元化先生、钟叔河先生相比,孟泽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识,只是更为具体。孟泽先生在书中说:“郭嵩焘之不同于李鸿章等,在于他在惊羡坚船利炮之余,考虑得更多的是人家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就是说,郭嵩焘能在西洋器物强大的背后看到西洋文明之“本”。用郭嵩焘的原话说就是:“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探求西方文明之本的同时,郭嵩焘也积极反思中华文化的缺失与不足,他对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重农抑商制度,甚至“圣人之治”的传统,都提出质疑。这些也都成为众人攻击郭嵩焘不爱国的口实。
爱国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高的道德规范。可是,爱国就是固守“祖宗之法”吗?爱国就只是抵抗外来侵略吗?
当代著名史学家袁伟时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爱国者。另一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是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才能够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袁伟时先生的这种论断可谓真知灼见,不仅拓宽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同时也给郭嵩焘这类可贵的历史人物以恰当的定位。
4.另一种勇气
郭嵩焘曾在一首诗中自慰:“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一份来自心底的自信,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无奈。为何非得“百代千龄”之后才能被世人理解?因为他的见识远超当时的时代,他的思想不融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从英国返回之后,他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世界都得罪了。然而,郭嵩焘依然不妥协,不退缩,不从众。在名节大于生死的传统社会,郭嵩焘能如此特立独行,坚持真理,这就不只是才智和见识的问题,更是一种可贵的勇气了。
勇气,就是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魄。一般而言,勇气被定义为“不畏艰难”,就是能攻坚克难,比如,能打垮敌人堡垒,能完成艰巨任务,能解决社会难题等。比如,曾国藩在晚清遭受内忧外患之时,勇于受命于危难,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这就是一种“不为艰难的勇气”。
其实,还有另一种勇气,那就是“不惧误解与邪恶的勇气”。当代教育学家吴康宁先生对这种勇气做了这样的描述:担当者明明知道自己的选择多半很难得到人们普遍的公开的积极评价,反而有可能被质疑、被指责、被污名化,甚至被恐吓、被报复,但为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真理,为了心中所存有的那份良知,而依然选择担当,无所畏惧,坦然面对。这段话并不是具体描述某一个人的,但我们在读过《独醒之累》之后,了解了郭嵩焘的人生际遇之后,不得不感慨:郭嵩焘就是“不惧误解与邪恶的勇气”之典范。更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勇气并非源于青年的锐气,而是坚持至生命的最后。海外史家汪荣祖先生就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中说,郭嵩焘“的晚年仍然相当坚持己见,不随世俗转移,多少表现出知识上以及道德上的勇气”。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融入整个世界之中,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嵩焘的那些“先知先觉”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可是,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却鲜有郭嵩焘那样的勇气之人。阅读郭嵩焘,学习郭嵩焘,并非学习他如何建功立业,而是学习他如何形成不凡的见识,学习他如何养成坚强的勇气。正如孟泽先生在书中所说,郭嵩焘“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芬芳悱恻的灵魂,一种超越了时代的有关中西文明的见识和思想,而不是令人回肠荡气的不朽功业”。
作者简介:余孟孟,《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教育学硕士,文史爱好者。在各类教育期刊发表文章60余篇。
来源:红网
作者:余孟孟
编辑:王津
本文为湖南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