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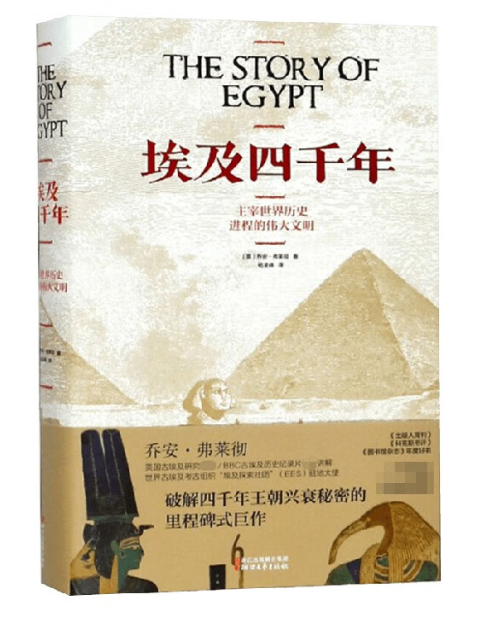
一、只差六年,他就在位执政了一百年
《埃及四千年——主宰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文明》
乔安·弗莱彻 著
公元前2278年,佩皮二世继位,其时六岁。
参加仪典的祭司、大臣和王亲国戚,似乎大都没将这个羸弱、懵懂的孩子,与自己的命运作太多联想。古埃及王国的权杖传至此时,已是一根频仍易主的接力棒,眨眼间就可能传递到下一任手上。为官一世,究竟要参加多少次这样的加冕,跪拜多少位这样的新王,没人说得清。不过,这一次所有人都错了,大错特错了!此刻蜷缩在王太后腿上的这个面带惊恐的男童,不仅将穿越在场每个人的余生,甚至还将横贯他们子孙的生命,在接下来漫长的九十四年里,将权杖牢牢握在手中,成为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
古埃及的政治设计,如今看上去有些霸蛮。先王们想要的不是“君权神授”或“政教合一”,而是直挺挺硬邦邦地宣称自己就是神灵,是天上某位主神的人间化身。其政权,当然也就是天庭的派出机构,冒犯王权,就是挑战天庭。因而古埃及平民与王族之间的区分,不是贫富,不是文野,也不是尊卑,而是人与神两个不同的物种,二者间不可逾越。先王们要将如此生硬蛮横的故事讲下去,让人信,除了靠祭司们装神弄鬼,还得有一套规矩与律令落地支撑。首先就是婚配,天神只能和天神交媾生育,才能保证每位国王种系纯正,来路可靠。如此,国王就不能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偶来搞海选了,王后只能从王族近亲中选配。于是便有了兄与妹、弟与姊,甚至叔父与侄女、舅父与甥女结合的夫妻。世代相姻的近亲繁殖,必然导致基因变异、生命力衰退。到了古王国晚期,病弱、短命的王位继承者越来越多,极大伤害了王族作为天神化身的公共信誉,甚至使之日渐沦为一个不攻自破的笑话。及至佩皮一世,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天荒娶了一位平民女子为后。佩皮二世是否就是这桩惊世骇俗婚姻的伟大成果,至今不可确考。但其强大长久的生命与牢固漫长的执政期,却是埃及六千年史上绝无仅有的。
佩皮二世既说不上荒淫无度,也算不上离经叛道。相比一世,他更谨守祖制,勤勉为政。他甚至没有跟进佩皮一世,迎娶平民女子为后,而是像先祖那样,老老实实娶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他也遣使睦邻,驻兵戍边;他也造塔敬神,激励农桑。但其作为一位国王的般般努力,却抵不过尼罗河水的逐年减少,河谷绿洲的逐年歉收;抵不过三面边境的连年烽火,环伺蛮族的连年进犯……
确实,佩皮二世活得太长久了!准确地说,是作为国王活得太长久了!大臣们一代一代死去,世袭顶替到身边的,永远是一张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子孙们也一辈一辈死去,怯生生来到跟前的,永远是一双双无望而怨怼的眼睛。王宫里进进出出的人,不知道王座上那个半神半人的生命,已经活了多久,还将活多久。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一定活不过他。子孙们开始逃离王宫,既然继位无望,那就不如另筑一座宫殿及时行乐;大臣们开始逃离王城,既然谁也走不近君王,那就不如躲得更远些,免得在他身边被看不顺眼甚至被猜忌;连祭司们也逃往外地修建宅院,不再迷恋那座神圣的祭坛:几乎所有的权豪势要都选择了远离。偌大的一座王宫,除了四壁摇曳的灯影,就是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阴森凉风。日夜陪伴老国王的,只有看上去空荡荡,感觉上沉甸甸的无边寂寞。他当然可以颁旨令祭司、大臣,令所有逃离的人都回城宫,可即使都来了,又能说些什么呢?那背书似的曲意奉承和虚伪祝福,除了平添高处不胜寒的另一种寂寞,绝对暖不了自己的心。其实他早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同他说话的,只有他自己。只要他还活着,就必定活在寂寞里,那种生命与权力纠缠的无边寂寞里。
古埃及有执政满三十年便举办盛大庆典的传统,但多数的国王,都无福享受这份无上的尊荣。能举行两次大庆的,自然是凤毛麟角,而能举行三次的,亘古至今,只有佩皮二世一人。此时他已九十六岁,当浩浩荡荡的人群将他和神像一并抬起,行进在宽阔的尼罗河谷,他抬眼望了望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又低头看了看缓缓流淌的尼罗河水,慢慢闭上双眼。人们不知道他是在人声鼎沸中沉沉入睡了,还是陷入了对遥远往事的无尽回想。总归不会有人猜想,他们的国王是不是寿终了。谁都相信,他还能活得更久长!
其时,古老的埃及也像这位昏昏欲睡的国王,在漫长的寿命中渐渐衰老,摇摇晃晃跌入另一个时代。设想:佩皮二世若是一位锐意变革、开拓新局的君王,这近百年的执政时间,应该足够他挽狂澜于既倒吧?如不是他一人执政近百年,其间又是否能碰上一两位中兴之君,使国家再现辉煌?古王国晚期的埃及,究竟需要百年执政的佩皮二世,还是另几位更年轻的国王?佩皮二世究竟是一位稳健老到的明君,让国家苟延残喘近百年,避免了断崖式的败亡,还是一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昏君,耽误了埃及“返老还童”的最后机遇?
一位百岁之君的寂寞,与一个六千年古国的寂寞,会是同样的不可承受吗?于我而言,应该会更恐惧百年执政的那一种。

二、几乎所有罗马君主都在找:人民在哪里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
玛丽·比尔德 著
“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
这是西塞罗一生最著名的演说的开篇。作为古罗马时代重要的金句,它在拉丁语世界流行了两千年。
公元前65年11月8日,在罗马城中的朱庇特神庙(传说此庙为罗马创立者罗慕路斯因祈神应验而建),罗马执政官西塞罗面对元老院三百多名元老,义正词严地揭露一场针对他的谋杀和企图毁灭罗马城市的阴谋。被指证者,是坐在对面的喀提林,一位两度与其竞选罗马执政官的政治宿敌。
喀提林出生于货真价实的蓝血家族,其门第,高贵到能与罗慕路斯扯上关系。与之相比,西塞罗只是罗马城边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一说祖上也曾出过骑士)。靠着聪颖与苦读,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宏伟志向,他逆天改命,成了罗马最出名的律师;又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天才的演说能力,他挤进了元老院,且在执政官竞选中连胜两任。到了西塞罗时代,罗马的执政官,不再由元老院指任,而是由市民选举。出身寒素的西塞罗能获胜,当然是人民的胜利。而被人民抛弃的喀提林,不仅丢失了民心,且为竞选耗尽了家财,陷入困境,因此决定铤而走险。
西塞罗出示了喀提林策划暗杀的书信,以及他企图毁灭罗马城的证据。他言之凿凿,雄辩滔滔,不仅使喀提林阴谋败露,而且让他面临审判。喀提林趁乱逃到城郊,组织起一支反叛军队,以人民的名义与罗马军团作战,最终战死疆场。有趣的是,喀提林在城外率领人民浴血奋战,西塞罗在城内代表人民宣判阴谋参与者死刑。尽管这一宣判未经审理,有违法律,但人民依然满城欢庆,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呼西塞罗为“罗马之父”。
那是西塞罗最高光的时刻!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祭司、执政官、律师、诗人和雄辩家,被人民拥戴为“当代罗慕路斯”“罗马之城的伟大守护者”。然而,西塞罗做梦也不曾想到,仅仅五年后,他就被踢出了元老院,被放逐到了距罗马千里之外的蛮荒地界。人民似乎幡然醒悟:西塞罗当初处死喀提林的同谋,未走正常的审判程序,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践踏了人民的权利!没人还记得,自己也曾为这个“果断英明”的决定激情澎湃,山呼万岁。
后来是恺撒,虽未执杖称帝,但架空,甚至实质上废弃了元老院。形式上虽有所谓的“三头同盟”,实际上朝纲独断。元老院失去了更多权力,人民却更拥戴这位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再后来,元老院元老布鲁图斯杀了恺撒,恺撒的指挥官安东尼杀了西塞罗,其间都有民意的鼓动,至少,他们都高举了人民这面旗帜。公元前44年,西塞罗的头颅和右臂被送回罗马,钉在城中广场,汹涌的人民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凌辱其残缺的尸体,狂欢通宵达旦。
在罗马元老院盛极而衰的一百年里,“人民”是一个戏份很重却又面目含混的政治主角。每一场重要的戏码,都被人从台后推至台前,声嘶力竭地表演,但直到剧终,你也说不出人民是谁,人民在哪里,人民属于谁(是西塞罗还是喀提林,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是共和还是帝制)。人民上演的,究竟是历史悲剧还是人间喜剧。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追问,这串问题显得陈旧迂腐而且没有答案。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针对某一段具体的历史如此发问,就显得有趣并有了价值,就像《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的作者,玛丽·比尔德所做的那样。
比尔德是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一度是剑桥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其著作,考据功力深湛,质疑精神执拗,为史学界所推崇,同时又以其卓越的历史还原力和生动风趣的叙述,为阅读界所追捧。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学术网红和破圈教授。比尔德的史学观旗帜鲜明:历史写作,就是一场与史事、文物和历代史学家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或是更加明晰,或是更加疑惑,但这两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的过程。比尔德常在书中摆出自己的结论,同时也摆出自我的质疑。读她的著作,你不仅能愉悦地分享其在古代史中寻找到的思想灵光,还能陪伴她一路寻寻觅觅。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书名,来源于罗马一个最常见的字母组合——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直译即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罗马人将这个缩写绣在军团鹰旗上,铸在下水井井盖上,甚至刻在垃圾桶上,而且这种传统,自公元前一二百年就滥觞了。这究竟是古罗马人的政体广告,还是执政箴言?或许都是。无论元老院与人民这两个政治角色,在历史演进中是否真正权力对等,是否也曾“越俎代庖”,或者“挂羊头卖狗肉”,但能将人民与元老院赫然并列,于大街小巷向市民宣告和承诺,作为一种历史政治现象,已经具备了可深入研究的价值。尽管执政者与人民,是任何一种政体的基本关系,但古罗马的体制,至少是一种开创性的平衡实验。比如几乎在同样早的时代,孟子就提出了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并辅之以一套仁政的执政理念。但说到底,那只是思想家的案头学说,教育家的课徒教案,算不上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制度运行。
人民作为一种流动不羁却又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古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比尔德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的疑惑依旧比确定多。但她以丰满的历史细节、生动的历史场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具体性,逼使我们沉溺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这种沉溺和寻找,或许能让我们远离当代政治逻辑和语境,在更深远的维度上,独立思考“人民”一词在现实中应有的处境与使命。
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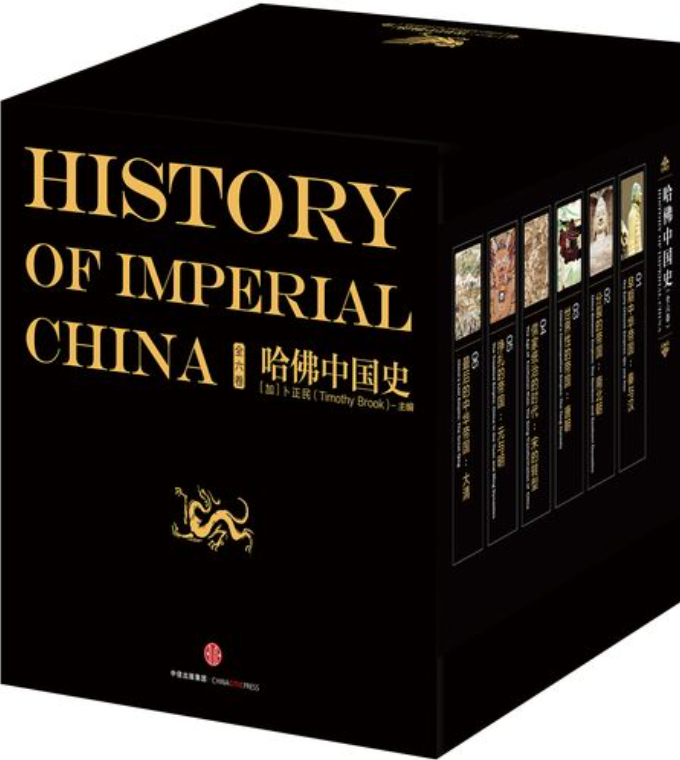
三、帝国是怎么炼成的
《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 主编
公元前239年,咸阳城集市的大门口,发生了一件万众瞩目的异怪事。吕不韦将刚刚编纂完成的《吕氏春秋》,齐刷刷摆在了集市门口,并在大门上挂了一个装有千金的袋子,悬赏能为《吕氏春秋》增删一字的人。集市原本每天车拥人挤,如今有了这千金悬赏,自然更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是否真的有人领到了这笔赏金,史书未载,但吕不韦《吕氏春秋》编纂完成的消息,却全咸阳城及至秦地全境,尽人皆知了。
当然,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吕不韦广罗各家各派的名师大家,收为门客,闭门编纂,费时六年,终成一部博大精深的旷世奇书,按理当献于朝廷,供于太学,现今置于屠狗宰牛、售鱼鬻虾、引车卖浆之徒云集的大市场,且悬赏千金以求修正,怎么说,都觉得南辕北辙找错了地方。但素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吕不韦,要的就是这个广告天下的轰动效果。他当然知道集市不会有几个真读书的人,但那地方人多嘴杂,什么事都长了腿似的,传得又快又广。他编这部书,可不是给学究们放在案头作研究,而是给即将诞生的一统帝国,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文化蓝本和精神指引。他要以史为鉴,为新生的帝国制定一套思想文化的治国纲领。所以这部书不能走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的传统路径,必须即行刊布于天下。
纵观吕不韦一生,就没干过一件入不了眼的小事。即使用了蝇营狗苟的手段,谋求的也是经邦济世的大事。他将身怀六甲的赵姬献给始皇帝他爹(一说),谋的是改朝换代的大局;他将身怀异秉的嫪毐献给始皇帝他娘,躲的是身首异处、门灭九族的大祸;他将身怀异术的李斯献给始皇帝,立的是辅佐其江山一统的大业……吕不韦早就预料了自己的失宠、失势,甚至命祭帝国的结局,所以他焚膏继晷地编辑这部经天纬地的大书。因为只有他意识到,呼之欲出的帝国,需要一套与之一同诞生的思想文化经典。纵世上饱学之士、天纵之人齐聚秦境,也只有他才能举旗担纲这部国之大书。因为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甚至不是包容百家的气度,而是格局、见识、理想,是缔造天下一统大帝国的豪气和方略。《吕氏春秋》完成四年后,吕不韦饮鸩自尽。他应该是面带微笑而去的,因为他一生为之殚精竭虑的帝国,此时已雄浑喷薄于方圆九州。常说人生为一大事来,而吕不韦的所为之事,才是亘古至今真正的中华大事。
更早谋图秦国霸业的人中,功绩显赫者,首推商鞅。是他用一套完整的扶农强军政策,将秦国变革为一个粮足兵壮、武器精良的军事强国。虽然作为改革者,他最终被车裂,但其改革的思想和变法的成果,悉数被后来的当政者继承。决定秦国能否成为帝国的是商鞅,决定何人何时缔造帝国的是吕不韦,决定创立一个怎样的帝国的是始皇帝。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吕不韦一生思维缜密、手段凌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卧薪尝胆成就绝世功业,可他骨子里,信奉与推崇的却是老庄哲学。在诸子百家中,他选择了道家作为《吕氏春秋》的思想统领,倡明未来治理帝国的文化精神,应是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吕不韦所为之事尽显法家手段,所求之道却是黄老学说,这究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撕裂,还是一种奇妙无比的融汇?是他觉得立国须用法家的峻法厉刑,治国却需用道家的无为而治?或者他已从秦国施行法家的迅疾崛起中,看到了官逼民反的深重危机,企图用这部探讨治国之道的著作,隐晦地对始皇帝进行提醒与规劝?若真如此,作为帝国的谋划者与催生者,吕不韦用心之深邃,用情之恳切,真是可鉴天地,可昭日月。意气风发的始皇帝,自然是听不进这一番劝导,理会不了这一份苦心的,他义无反顾地在法家的道路上疾进,于是,便有了辉煌而短命的大秦帝国。假如当初始皇帝听取了吕不韦的想法,将道家作为帝国的文化思想,大秦帝国会如此匆促而亡吗?而一个施行无为而治的大秦帝国,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样子?会像大唐帝国那般强大繁荣吗?由此肇始的中华帝国传统,又该如何书写和延续呢……
如果没有大汉帝国的果断接续,中国人的帝国梦想,或许早就破灭在了秦代。汉代坚定继承了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并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打造了第一个中华帝国的完备、成熟版本。大汉帝国的政治家们,既没有接受吕不韦推荐的道家,也没有继承始皇帝施行的法家,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精神治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以此深远影响了中华帝国史。回望两千三百年中的各个帝国,分别由法、儒、道三家思想轮番主宰,但无论谁主其位,都是一家统领,其余并存,或者罢而不黜,发挥潜在影响。
《吕氏春秋》是否影响了大唐帝国?如果是,那也没枉费吕不韦的一番心血!
诱使我作以上讨论的《哈佛中国史》,严谨地说,只能算一部《中华帝国史》。如果要冠以“中国史”之名,是断然不可以如现在这般从秦汉起笔的。中国史与中华帝国史之间,差不多存在两千年的时间差。这一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不可以忽视。所以定下这个书名,大抵是为了和《剑桥中国史》打个擂台,或者蹭蹭热度。然而哈佛作为世界知名学府,其出版社素以学术严谨蜚声,如此操作确乎有点跌损身份。其实就叫《中华帝国史》,或者《哈佛中华帝国史》,既名实相称,又独特醒目。或许与费正清、崔德瑞相比,卜正民、陆威仪、库恩、罗威廉等新生代的汉学家,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因而难免装怯作勇。其实着眼中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历史,对读者是有特别意义的。虽然中国也产生过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但大一统的帝国还是历朝历代的理想和追求。即使是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谈及国事,依然以一统天下的帝国为荣耀。
如果希望了解中华帝国的理想赓续和治理变革,这部六卷本的史书是值得一读的。原因之一,全书专注于帝国的创立、运行和更迭,省略了许多不相干的事件与细节,主脑明确,头绪清晰,腾出笔墨聚焦帝国史事,勾勒了一幅新异、简洁的中国主要王朝图谱;原因之二,将中华帝国置于世界历史版图,不仅关注了世界各帝国的异同,而且揭橥了中华帝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原因之三,使用了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征引了海外研究的新文献,尤其是一些帝国史研究理论和数据模型,使得文本丰满、新颖和生动。
不过,作为一本中国通史的入门书,《哈佛中国史》并不合适。初习历史者,建议还是读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或者《剑桥中国史》。

四、君士坦丁堡的叹息:请神容易敬神难
《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著
君士坦丁大帝接到近卫军报告时,新帝都已陷入暴乱。街道上激愤的教民,疯了一般冲进教堂,殴打教士,捣毁圣物,甚至点火焚烧建筑,滚滚浓烟笼罩了整个君士坦丁堡。
《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纷争一直不断,尤其是与古希腊多神教的冲突,还时有激化。但出乎君士坦丁意料的是,这一次酿成暴乱的冲突竟发生在基督教徒之间,千真万确的自家人打自家人。随着基督教影响扩大,地位攀高,教士们的教义分歧日渐公开化,以至滥觞为教派之争。在关于耶稣与圣父的关系上,正统派和阿里乌派斗得水火不容,导致了这场教众的围攻殴斗。目睹亲自选址、亲自督造的新都城,没过几年便惨遭浩劫,君士坦丁心痛难忍。如果是外族入侵,城破城毁也就罢了,想不到竟是被一群基督徒打砸抢烧,真让他有点悔不当初!公元313年,是他说服李锡尼共同签署敕令,赋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这才过去多少年,教士教徒们竟为一点教义分歧大打出手,弄得新都城一派狼藉,实在有些“稀泥巴糊不上壁”,让人顿生恨铁不成钢的怨尤。
然而大帝就是大帝,他知道军队再勇猛,刀剑再锋利,也不能用来解决教义纷争。为了罗马帝国,他只得按下怒火,从长计议。他亲自出面,邀请各地主教赶赴尼西亚开会,坐下来商讨教义分歧,以期达成共识。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一改叱咤风云的做派,谦逊地坐在听众席后排,聆听主教们慷慨陈词,并协调各方意见,艰难通过了《尼西亚信经》。这便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大会,史称“第一次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皇帝的面子和权力,促成大会确立了“圣子与圣父同质”的正统教义,短暂平息了教派纷争,同时开启了世俗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皇权与教权相互媾和或彼此争斗的历史先河。
实际上,正统派与阿里乌派的争端,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烟消云散。倔强的阿里乌主教虽被斥为异端,却颇受教众拥戴,且教派愈遭打击,教徒愈是坚定,反抗也愈激烈。由此引发的教派间冲突,各地仍旧无法禁绝。前半生浴血征战、平定天下的君士坦丁皇帝,后半生却要深深纠缠在宗教事务中,这应该是他无法想象的。他甚至连自己究竟要不要受洗,何时受洗,也一直犹豫纠结。直到临终,他才接受了阿里乌派的洗礼,褪去镶饰金边的紫色皇袍,穿上了基督徒的白色洗礼袍。遵照遗嘱,他死后被安葬在使徒教堂,十二使徒的圣物墓分排两边,他则安卧在中间,以示自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
究竟是哪种因素促成君士坦丁皇帝力排众议,执拗地将帝都东迁?在政治、军事、宗教三者中,我们无法确定谁排第一,但基督教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时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与影响,远甚于西方。读历史,总能挑逗起我们对关键节点和事件假设的冲动,在一种事后逻辑的思维快感中进行质疑和演绎。但凡读过君士坦丁传或者拜占庭史的人,大抵都会设问: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坐大并皈依基督教,那基督教的命运该是如何呢?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决意迁都,那世界的格局又该如何呢?有人说,除了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如果站在基督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言,这一排序自有其道理。
是君士坦丁为拜占庭帝国请来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并将皇权和神权捆绑在一起。在拜占庭长达一千一百年的历史中,君士坦丁的生命基因早已断绝,但精神基因却世代相因、源远流长。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并非每一位都信仰基督教,都属于正统教派。其中也有人信多神教,一登基就拆毁焚烧基督教堂;也有人属于阿里乌派,一掌权便把正统派教士扫地出门。但无论他们信什么教,属什么派,终其一生,都得与基督教生死纠缠,只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有基督教在场。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做大了基督教,并在后来将之立为国教供奉在庙堂中,其帝国是否能薪火不绝长达千年?后来那些或篡位或被士兵推举的蛮族皇帝,他们换主人而不换门庭,始终打着拜占庭帝国的旗号,或许正因为有基督教这一强大的精神基因存在。如此说来,君士坦丁不仅是罗马帝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也是第一个用意识形态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大国领袖。
阅读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需要备好耐性和心情的。那长达千余年的王朝,反反复复上演的,都是反叛与征讨,谋杀与篡位,同性恋与通奸,陷害与殉道……你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人名,也记不住那些似曾相识的史事。如同一部随时都可以剧终却总也不剧终的连续剧,你看得昏昏欲睡,但又无法真的睡去。只有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兵临城下,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被一举攻破,你才会精神一振,睁大眼睛观看这个古老帝国如何轰然坍塌。
灿烂的文化和腐臭的人性,构成了这段漫长历史的两个极点。一方面,你会为那些宏伟辉煌的建筑所倾倒,为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典所震撼;另一方面,你会为那些深不见底的阴谋所胆寒,为那些没有尽头的杀戮所麻木。史学家莱基曾在《欧洲道德史》中称拜占庭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莱基虽有其道德偏见,但所述史事却是基本吻合的。
莱基给拜占庭人下了一个定义,即“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谁的奴隶?或者自甘沦落为谁的奴隶?是草菅人命、嗜血杀戮的皇权,还是禁锢人欲、禁绝自由的教权?或者是二者时而媾和时而争斗的权力合体?伟大的君士坦丁,为后世设计并打造的神的王朝,难道就是一座驯养奴隶的囚牢?漫长的帝国史,难道就是一部奴隶驯化史?
这,才是拜占庭的历史痛点!
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这个振聋发聩的判断,撇开拜占庭的历史,置放在当代社会中,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
《拜占庭的新生》的作者诺里奇,是不赞同莱基的观点的。他用皇皇三部曲,企图再现拜占庭的辉煌。诺里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也是一个超级历史发烧友,因对拜占庭的热爱而长期从事业余研究。但非专业的历史叙述,既缺少生动的细节,又缺乏警策的思想,使其著作读来干涩沉闷。在硬着头皮读完这部《拜占庭的新生》后,余下的两部,就只是一目十行地翻翻了。其实,即使是一段冗长沉闷的历史,也是可以写得很生动精彩,让人不忍释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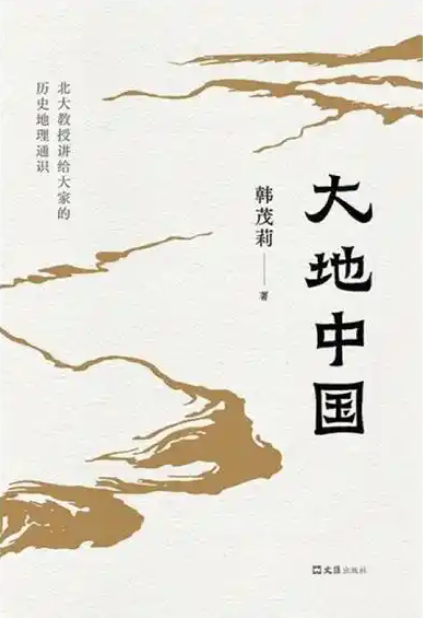
五、一个量产皇帝的地方
《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武川,史称镇,今为县,内蒙草原、阴山北麓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驾车兜一圈,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个出皇帝的地儿,可偏偏连续二百年,这里出了一大群皇帝!究竟是九位、十位还是十几位,各人算法不同,但由武川子弟建立的王朝有四个,这是板上钉钉的。放眼华夏九州,这种皇帝辈出的地方,怕是只有这一处。
堪舆师们理当不会错过武川。历史已经确凿证明这里风水上佳,他们只要看山看水说出点门道,便是难得的风水案例。我还真查过几本风水书,就是没看到说武川的。或许这等皇帝辈出的绝顶风水,永远天机不可泄露。
也听说曾经有个和尚,放着经不念,成天抱着一本面相书啃。天长日久,觉得自己功夫了得了,便去游走世界闯荡江湖。到了武川这地方,天荒远,地穷寒,街上行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可一看那一张张木讷呆板的脸,竟都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面相。这当然不可思议!和尚大惊,继之大惑,然后大悔,悔不该当初信了这骗人的相书,误了自己吃斋念佛的少年功。如出一辙的故事,我还听过一个,讲的是洪秀全起事之前的金田县城。说到底,还是天机不可勘破,即使破了,也没人敢信。
不信风水的陈寅恪,倒是用心研究过武川,并由武川现象提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全新概念:“关陇集团”。他从鲜卑军事豪强与汉人政治豪门结盟的角度,解释了武川帝王代出的原因,并对中古门阀制度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卓有建树的学术探讨。
公元424年,柔然可汗大檀听说北魏皇帝死了,以为天赐良机,亲率六万铁骑进犯宿敌,企图一战灭北魏。十五岁的新皇帝拓跋焘力排众议,领两万兵丁迎敌。少年皇帝亲冒矢石,率先冲杀,使北魏军心大振,射杀敌军大将于阵中,以少胜多大败柔然。五年后,拓跋焘再领大军与柔然决战,挥师突进三千余里,斩敌数万,受降军三十万余,缴戎马百万余。拓跋焘为安置这庞大的降族与马匹,沿阴山北麓圈地定居,使其或耕或牧,繁衍生息。为防范柔然人反叛起事,北魏设置了武川、怀朔等六镇,选派鲜卑贵族和汉人豪族子弟驻守。西魏开国皇帝元宝炬、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先辈,都是当年六镇的镇守者。胡汉混合的镇守体制,使鲜卑的部落制与汉人的军护制相融合,既保存了胡兵个体作战勇猛的优势,又发挥了汉军整体作战的长处,六镇军力因之大增。北魏都城东迁后,频仍征伐山东,致使六镇地位下降,军饷与供给时有不济,激起六镇兵变。北魏设置六镇为防范胡人,没想到却养虎成患,到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军事豪强,其代表就是“八大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是宇文觉的爹,李虎是李渊的爷爷,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公。这些六镇豪强与关陇豪族相结合,形成了中古时期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西魏、北周、隋和唐四朝的开国之君,均出其中,很有点“皇帝轮流当,今天到我家”的味道。而武川豪强,则是这个集团的绝对核心。
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看,武川正好在胡与汉、农与牧的交接部,因而承袭了农牧结合的生存方式、胡汉融汇的文化习俗。胡人尚武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不受儒家伦理约束的政治斗争方式,铸造了这个集团有别于任何汉人集团的政治理念和手段。武川的这些豪强,其鲜卑姓氏究竟是北魏赐予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其血统究竟属胡属汉,至今仍无定论。但即使其基因百分百属于汉人,精神血统也绝对已经胡汉杂交,且显现出了强大杂交优势。隋、唐两朝的那种宏阔雍容、豪迈爽朗,是此前此后任何汉人政权所少有的。蒙古草原与阴山,作为一种历史地理标志,其意义也绝不囿于堪舆学范畴。或者可以说,武川所出的这些皇帝,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地养的!古人常说欲成帝国大事,必据“根本之地”。隋、唐可以再统中华再造帝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据有了关陇这片“根本之地”。
对于地理与历史乃至文明的关系,无论什么学派的史学家都绕不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创造历史的人是水土按自己的可能养育出来的,那么历史也只能按照地理所可能提供的条件发展。当然,要说清某一地理特征如何具体影响某段历史,的确十分困难。多数的史学家,只能笼统言之,或者将自然地理作为一种影响因子提出来,具体影响,则由读者自己去思考。
读《史记》也会碰到大量山川河流的描写。在司马迁笔下,这些形貌生动的地理,具体影响了历史什么,如何影响,也时常语焉不详。究其根源,地理是一种亘古、巨大的自然存在,对其所在之地的居民的影响,是长久而潜在的。地理先以自然的逻辑影响人,然后人以人文的逻辑影响历史,只有极少量的历史事件,是以自然的逻辑直接影响历史的。此一特征,使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相对缓慢。但它近来似乎有成为显学的迹象,读者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了。
韩茂莉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且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声名颇显赫。其著作《大地中国》,篇幅倒不欺人,装帧也不唬人,所谈的二十六个专题,也都是地道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尤其涉及农业地理的篇章,即使力求晓畅通俗,仍能见出文献考据和田野勘察的学术功底来。所有专题以历史纵轴辑合,虽无咬合式的前后关联,但也能显露出时代更迭的内在逻辑。这些专题,或宏大,或奇巧,叙述一律轻松有趣,读来并不伤神费力。作者在后记中也表达,希望将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推向社会,显出一种谋求破圈的努力。既然从主观到客观,这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故其消遣的阅读属性,便在情理中了。
(此文为读书札记集《乱翻书》部分章节)
来源:红网
作者:龚曙光
编辑:高芹
本文为湖南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