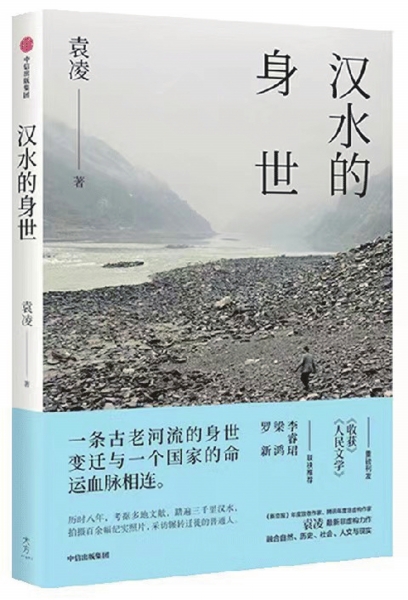
味蕾敏感的北京人发现,近些年北京的自来水口感舒适了很多。这是因为水的硬度降低了,而水的硬度降低,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把汉水引向了京、津等北方多地。
“到今天,北京市民打开厨房水龙头,每一滴水中都有70%来自汉江,而在天津则是全部。”《汉水的身世》中,袁凌告诉了大多数北京人和天津人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
汉水,这个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民族同名的河流,实际上已成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母亲河。
在《汉水的身世》里,非虚构作家、前知名调查记者袁凌记录下了这条河从古至今有过的付出。
3月25日晚,第八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公布,《汉水的身世》获年度作品奖。
离开家乡20多年后,袁凌在北京重逢了汉水
少年时,袁凌差点在汉水淹死。袁凌的老家没在汉水边上,汉水有条支流叫坝河,坝河的发源地在陕西安康平利县,平利县有一个名叫“筲箕凹”的山村,13岁以前,袁凌就在这个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的山村。13岁,袁凌到了安康上中学,第一次见到了汉水。
“在白光光的大堤下,似乎没有什么颜色,那宽度是我从未见过的,相比之下我不过是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小小衣物。”
这是汉水给他的第一印象。当时,他并不知道日后会一次次走近、走访这条河,更不知道还会为这条河写一本书。这条河,袁凌第一次见它之前,就对它有过向往。他从小就听父亲说过这条河,说他曾横渡汉水,且游来游去。父亲只说过他横渡过汉水,但他没说横渡的细节,这导致效仿父亲壮举的袁凌差点淹死。大难不死后,他才知道当年父亲游汉水时,是很多人一起游的,而且,旁边还有船跟着,游不动了,人可以爬上船休息。但,袁凌游汉水,却只是他一个人。幸运的是,在他最后放弃挣扎、下沉的时候,他的脚踩到了石头。
后来,袁凌翻越秦岭,去了省城西安上大学。当时他以为自己远离了汉水,特别难过的时候,还有几次坐大巴返回安康,只为了在熟悉的汉水边走一走。后来,他才知道,其实,在西安,他也没真正离开过汉水,他在西安打开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有一部分是通过引水工程从汉水引到西安。
后来,袁凌在上海读研,在北京读博。2003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没读完,他去了创刊中的新京报。再后来,袁凌在《财经》、新浪网、《凤凰周刊》上先后任职。他的《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走出马三家》等报道,让他成为名记;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则奠定了他在非虚构领域的江湖地位。
袁凌没有想到,在离开家乡20多年后,在离家乡遥远的北京,他又一次和汉水重逢——只要他打开水龙头,水龙头里就有汉水的水不远千里流出来——袁凌在北京能够喝上汉水的水,是因为2014年通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在这个工程竣工、正式通水之前,袁凌走访了汉水沿线的水坝、移民、纤夫、船工、渔夫、污水处理厂,那时,他就触碰过汉水的躯体和灵魂,写出来长篇报道《汉水的祈祷》。
“每当我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我需要为它写些什么,记录它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它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它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在《汉水的身世》引言中,袁凌如是说。显然,在袁凌看来,他2014年完成的《汉水的祈祷》还远远不够。
汉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袁凌的父亲横渡汉水,是受了毛泽东多次横渡长江和湘江的影响。彼时,全国人民都效仿着横渡身边的大江大河。袁凌能够在北京喝上汉水的水,也和毛泽东有关。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出了南水北调的构想。因为这个构想,汉水中上游、湖北西北部的丹江口在1973年建成了一个库容可达290.5亿立方米的大坝。
虽然是长江的支流,汉水和另一条也是长江支流的淮河一样,历史上曾与长江、黄河并列,合称“江河淮汉”。这条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河流,河长1577千米,流域面积1959年前为17.43万平方千米,位居长江水系各流域之首。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从《诗经》中流出来的汉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堪称非常骄傲的历史,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著名学者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写道:“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称作“夏”或“华夏”,是因为汉水而得名。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技史》这样评述汉水:“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秦朝灭亡后,刘邦受封于汉江发源地的汉中,被封为“汉王”,在统一天下后又以“汉”为国号。汉朝建立起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前后四百余年经济、文化等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汉逐渐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称谓,我们写的字称汉字,服装为汉服。
袁凌查阅历史资料发现,战国后期楚怀王为商人颁布船运免税通行证,可以在汉江及其支流唐白河航行,并上达十堰郧县和陕西旬阳的汉江上游。可以推断,当时汉江中下游的商业航运已经十分繁荣。
汉水流域自古战事频繁,商贸交通繁忙,这里遗存有丰富的古道、古镇、古器物、古战场、古栈道、码头以及摩崖碑刻等多种形态的历史古迹,这使得汉水流域成为中国中部地区不可忽视的古代文明地带。
袁凌坦陈,《汉水的身世》出版前,他曾有意在书的腰封上称汉水为我们的第三条母亲河,但后来没有坚持,怕被认为是挑战大家,“这离大家的常识太远了,有点像炒作,但大家想一想,几乎整个北方都在喝它的水,这么一条河有没有资格称为母亲河?而且,历史上,它和我们民族关系那么深切,我们的民族和它同名,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凭什么不能称它为母亲河呢?”
大地伦理视角记录汉水的身世
3月26日下午,在长沙的藏相知文化记忆馆的分享会上,当时还没看到书的我,惊讶于袁凌PPT上手绘的像蛛网一样的发生在汉水身上的“调水”“补水”图。在《汉水的身世》第一篇《稀缺的血液》中,袁凌在小标题为“采血与补血”的章节里介绍了蜘蛛网一样的“调水”“补水”网络形成的始末。
“显而易见,在向北中国输血的同时,失血后的汉江靠自身已难以继续承担哺育这片平原的职责。为汉江输血势在必行,引江济汉成为现实的选择。”引江济汉,指的是从长江荆州段引水到汉水兴隆大坝的下方。光引江济汉还不够,引江补汉、引嘉济汉相继跟上。
“随着引江济汉、引江补汉工程的相继实施,汉江和长江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四边形的循环,原本的干流和支流、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水流也变成汉中有江、最终又归于江。如果引嘉济汉实施,则会组成一个包括长江、嘉陵江、汉江在内的更大循环。加上南水北调中线、引汉济渭,汉水已经由一条传统意义上的河流变成一幅水网,横跨东西南北。”
这个水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南水北调。袁凌写汉水入京第一站、北京西郊大宁水库,“水面格外平静,仿佛经过了126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它已经略为疲惫”。语句中透露出他对汉水的怜惜。
这是大地伦理视角下的汉水。如同袁凌其他非虚构作品直接以人为写作对象一样,他也把汉水当作是和人一样的生命体。袁凌尽他所能地还原了汉水被争夺、被伤害的全过程,也记录了爱汉水的人们为减少对汉水的伤害而所付出的努力。
河流,记录着文明的走向,一条河流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人类对河流的伤害泛滥全球。好在,从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开始,作家们加大了对包括河流在内的环境保护的发声,不至于使得更多的河流成为《寂静的春天》中所说的“死亡河流”。
《汉水的身世》之前,湖南作家、资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黄亮斌的《湘江向北》也是近几年出现的为河流发声的非虚构作品。“我对江河的态度是感恩和礼赞,我写湘江就是为了揭示河流对人类文明构建的普遍意义。”黄亮斌谈他为什么写作《湘江向北》。
《汉水的身世》中,袁凌和黄亮斌不谋而合,他在前言中说,他为写这本书而走访的8年,“又再度认识了这条母亲河,体会到她清癯美丽的品性和独一无二的身世,它的一部分偏枯逝去,另一部分却通向未来,预先哺育着我们”。
如何让我们的河流更好地通向未来?作家们的书中没有答案,但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思考。
对谈
我不想停留在温情主义的关切上

潇湘晨报:《汉水的身世》看完后,让我很感动的是,您把它当作一个生命体。我们很多人说某条河是他的母亲河,但也局限于嘴巴上说说,并没有真的把一条河当一个生命来看待。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把汉水当作一条生命的?
袁凌:很难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往,我在采访、做报道的时候,不管是对人还是对自然中的一些受到伤害的事物,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尤其是涉及的生态环保方面的报道,我对生态环保还是挺在意的。而汉江,从小在我心中它就不是作为一种资源在存在,对它最初是有一种情感的寄托,到后来觉得和它有一种情感的交流。比如说,从远方回老家,看到它就有一种安定感。我还有几次在外面有些事很难受,特意回去,在江边走一走,疗伤。尤其是在西安那几年,有两次我都是坐几个小时大巴,翻越秦岭,到汉江边住两天,确实有一种疗愈的效果。这样,你跟它之间,就有情感的交流。当我有想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生命体来书写。它本身是一个生命,同时也是很多生命的集合。
潇湘晨报:特别是这本书的书名,一看就知道您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资源看待。
袁凌:2014年,我写汉水的那个长报道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个长报道的标题是《汉水的祈祷》。只有生命,它才会祈祷,它是有血有肉,有疼痛、有别的感受的。这不仅是一种拟人化,比拟人更深一点,我说它有感受,不止是修辞,我是真的觉得它要承担、要付出,它会呼吸、会感觉。所以,那篇长报道的标题我就用的是《汉水的祈祷》。到写书的时候,怕别人误会祈祷和宗教有关,就没用之前的标题,想了很久才想到用“身世”这个词替代,“身世”这个词稍微平和一些,但俨然也可以看出我是把汉水作为生命体来写的。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是不会写这么一本书,顶多只会写一篇赞美汉水北调大工程的文章。
我对汉水的感情,可能真的就是把它当母亲一样看待。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环境里,我们小时候会给树喂饭。比如说家门口的梨树,它上面有些小眼,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吃饱了,就给它喂点饭,喂到那些小眼里。我小时候身体不大好,拜了个很大的石头作干爹,每年也都会给那个石头喂饭。想起这些,我印象很深的,不是给它们烧纸、祭祀什么的,而是给它们喂饭、酾酒,真的好像它们是能够吃饭、能够喝酒的生命一样。
这次过年回去,让我很惊讶的是,三十晚上吃完团年饭,我哥突然跟我说,走,咱们去拜拜那棵树——我们那里山上有棵很大的树,不知道多少年了,有几百年了吧。到快十二点钟,我们提着香烛、纸钱就去了,看到树上搭了无数的红绸,已经有好几拨人在那里拜了,蜡烛点着,烛光摇曳,他们拜完了才腾出地来,我哥、我嫂子上去拜。我本来另有信仰,对这个是有忌讳的,但是我又觉得它作为一个古老的生灵,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对它有一种感情,我尊重这种感情,虽然我没跪下去拜,但也作了个揖。
潇湘晨报:您刚刚提到如果不是把汉水当作生命,那就会写一篇赞美的文章。现在有不少人觉得好像只有赞美才是爱。
袁凌:如果你不能既感受到它的愉悦,又感受到它的疼痛、悲痛,感受到它的活力,或者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分不清自己是对它爱还是恨,就缺少切肤之感。
潇湘晨报:如果没看《汉水的身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汉水对我们国家如此重要,可以说它是一条被众多河流“淹没”的一条河流。
袁凌:汉水的近代衰落了,而它以往的辉煌又离现在太久。中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谁跟政治中心离得近,谁就显赫,是不是?大运河离政治中心比较近,所以,大家知道大运河;黄河,我们认为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也是不少政权的政治中心,所以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另外,我们的教材,提到黄河长江,就说是母亲河。所以几代人下来,母亲河的记忆就被黄河长江覆盖了。如果生活在古代,天天学的是江河淮汉并称,汉水就是和黄河长江一样的母亲河。
另外,我发现一个很遗憾、也很残酷的事实是,有很多人知道南水北调这件重大的事情,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水的来历。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水利工程,但不知道这个工程背后的事情,不知道这个工程和很多生命有关,仅把它当作是水资源的调动,而不是河流的摆动、摆弄,更谈不上知道背后的争夺。说得厉害点,有点饮水不思源。
潇湘晨报:我注意到书中有人回忆说以前的汉水是清甜的,“清甜”这个词,不说它有没有夸张,但我能够感觉到这个人对以前没被污染的汉水的爱。
袁凌:甜是一种味觉。像老家的食物一样,都有一种故土之情。食物之外,一般很少有东西被形容是甜的。甜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感情,比如我们说甜甜的爱。
潇湘晨报:这本书看完,我觉得你是在全方位地问诊汉水,而不是单从某个方面切入。
袁凌:我想把它作为生命体来书写的话,肯定不能单写某个方面,必须要把它的生命形态、境遇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书写。这就需要我分不同的章节、每个章节对应不同的课题,最后把它的各方面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呈现出来。所以,不能是人文感怀类、采风类的表达,我觉得都不足以真实地触及它的困境,不是真实的关切。我不想停留在温情主义的关切上。
潇湘晨报:书中有写到渔民的一些困境,而且篇幅不小。有人觉得时代发展的规律,必然有些事物要被淘汰,没必要对这些注定被淘汰的事物倾注感情。您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袁凌: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写说明书,没有什么事物是必要或不必要的。我写他,是因为他就在那里嘛。我写到他们,不表示说他们应该要怎样,我也写到他们跟鱼之间的相生相克,他们曾把一条中华鲟都吃掉了,他们本身对环境也是有所损害的,但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自己也裹挟其中,无能为力。那我把他们真实地展示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有一种文学性。这文学不是修辞,而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关切。这些渔民、移民本身就是这样,作为写作者我们有义务把他们的境况写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同情,虽然我更同情鱼。





